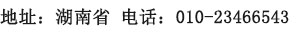一、食榧健体。
每个人都渴望长命百岁,追求健康,不生病是人类永恒的话题。据权威机构研究,香榧作为干果之王,有延年益寿,去病利气血之功效。
一、香榧是什么香榧产自北纬30度神秘地带,原产地在浙江绍兴古代地势高峻、山产丰裕的东白山麓。全球现存年以上树龄的香榧树有00多棵,主要生长在浙江绍兴诸暨。香榧子是一种红豆杉科植物的种子,其果实外有坚硬的果皮包裹,大小如枣,核如橄榄,两头尖,呈椭圆形。成熟后果壳为黄褐色或紫褐色,种实为黄白色,富有油脂和特有的一种香气,很能诱人食欲。二、香榧具有的功效1、驱除肠道寄生虫,香榧子中所含的大量榧子油,能有效地驱除肠道中绦虫、钩虫、烧虫、蛔虫、姜片虫等各种寄生虫。并且具有杀虫而不伤人体正气的特点,是有效的天然驱虫食品。2、治疗丝虫病,临床研究证明香榧对微丝蚴有一定的杀灭作用。
3、增强食欲,香榧中所含脂肪油气味微香略甜,能帮助脂溶性维生素的吸收,改善胃肠道功能状态,增进食欲,健脾益气。4、强身健体,提高机体免疫力香榧含有丰富的营养成分,可补充人体的必需营养物质。同时,香榧中大量的脂肪油具有润肺止咳祛疾,润肠通便的作用,有利于排除体内的致病毒素,达到强身健体,提高机体免疫力的效果。5、抑制白血病,榧子仁中所含的四种脂碱对淋巴细胞性白血病有明显的抑制作用,并对治疗和预防恶性程度很高的淋巴肉瘤有益。6、消除疳积、润肺滑肠、化痰止咳之功能,适用于多种便秘、疝气、痔疮、消化不良、食积、咳痰症状。7、抗艾滋病毒,近年对香榧的药用研究越来越深入。据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科研成果报道,香榧酯对艾滋病毒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即将作为制备抗艾滋病毒药物。三、食用禁忌:1、食用量:每天的食用量30-50颗。正常人平均每周干果的食用量不要超过克(克是果仁的净重)。
2、适合人群:一般人均可以食用。小儿和正在受寄生虫困扰的人可以适量嚼食。3、香榧子所含脂肪油较多,易滑肠,大便稀溏者不宜多食;素有痰热体质者慎食。4、香榧不要与绿豆同食,否则容易发生腹泻。5、香榧性质偏温热,多食会使人温热上火,所以咳嗽咽痛并且痰黄的人暂时不要食用。香榧是我国特有的珍稀干果,不管是古代文献的记录还是现代的科学研究发现,香榧具有极高的营养价值。“美容美颜”,“延年益寿”,“帮助消化”不是传言,而是确有其效。适用于脾胃虚弱,久病气虚,体倦肢软,食欲不佳者食之。对癌症也有一定的预防和治疗作用。坚果之王当之无愧!长期坚持吃香榧的人,身体想生病也难参考文献
1.《香榧的营养和功能成分综述》王向阳
2.《香榧种子成分分析及营养评价》黎章矩
3.《多不饱和脂肪酸的生理功能及安全性》鲍建民
4.《牛奶中的氨基酸含量及其营养价值》陆东林
5.《本草纲目》李时珍
6.《新修本草》苏敬
二、白云和乡茶。费翔的《故乡的云》曾流行一时,那一声声“天边飘过故乡的云,它不停的向我召唤”“归来吧归来哟,浪迹天涯的游子”,让许多海外游子听得热泪盈眶。听多了,耳熟能详,耳畔常常回荡起这样的旋律。不知道词作者是否知道“白云亲舍”的典故,这个典故出自唐代的狄仁杰,当时他的双亲在河阳别业,他赴并州,登上太行山,举目南望,但见白云孤飞,就对左右说:“吾亲所居,在此云下。”伫立瞻望,白云飘走了他才继续行走。看到白云就想念亲人,这是一种亲情,一种文化,“故乡的云”暗合此典,唱起“故乡的云”,才会有沉甸甸的感觉。
看到天边的白云,便想到白云下面故乡的青山,想到青山上漫山遍野的茶树,想到了故乡甜美的山泉,以及用山泉泡出的好茶。
这种茶的情结,和白云情结一样,让人魂牵梦绕。
我的故乡在东白山,主峰太白峰,东晋抱朴子葛洪曾在此炼丹,他的《抱朴子》把“太白山”列为全国名山,赵广信、禇伯玉等也都曾在此修道求仙。求仙得道之地,必有好茶。因为修道求仙分“内丹”和“外丹”两种,“内丹”就是练气功。“外丹”则以朱砂、雄黄、硫黄、芒硝等含汞、砷、硫、铅的矿物质炼丹,然后服用。这种“金丹”,含有比重很高的重金属,服用之后容易口干发热,少不得要喝大量水,饮用好茶,就是“标配”了。东晋的那些文人墨客们,都喜欢“嗑药”,就是服丹,脸红红的,比酒醉还荣耀。说一声“我有点发热”,那是身份的象征。“发热”了,说明他“嗑药”了,自然少不得要喝茶平衡一下。
东白山有好茶,龙门顶的茶叶,是天赐妙品,不知道葛洪有没有喝过,料想在太白峰修仙,太白峰的茶是不可能不喝的。我是喝过的,在诸暨工作时,故乡的好友偶尔会送我一些龙门好茶尝尝新。那茶确实好味道,估计杭州的“龙井十八棵御茶”也难以媲美。山里人实在,没有好好宣传,不会立一块“葛洪饮茶处”之类的牌子,有点“养在深山人未识”,实在可惜了。
白玉蟾原名葛长庚,母亲改嫁白氏,他也随之改姓,他是在道教历史上开宗立派的重要人物,创立了道教南宗,诗书画全能,自然也是喝茶的好手。我在美国看到过白玉蟾的真迹,那天求睹乡前辈杨维桢的书法,没想到杨维桢题跋在白玉蟾的诗卷上,便有了意料之外的眼缘,他的字确也写得仙风道骨。
他的《水调歌头》“咏茶”,从茶叶绽芽、采摘,到制作、点茶、品茶,描绘得非常生动传神:
《水调歌头咏茶》(宋·葛长庚)
二月一番雨,昨夜一声雷。枪旗争展,建溪春色占先魁。
采取枝头雀舌,带露和烟捣碎,炼作紫金堆。碾破香无限,飞起绿尘埃。
汲新泉,烹活火,试将来。放下兔毫瓯子,滋味舌头回。
唤醒青州从事,战退睡魔百万,梦不到阳台。两腋清风起,我欲上蓬莱。
特别是结尾“两腋清风起,我欲上蓬莱”,直言喝茶能够两腋生风,飘然欲仙,这应该是他的切身感受了。
在东白山茶乡长大的人来说,这个场景是最为熟悉、最为亲切的了。一声春雷,如同发令枪,春天的门轰然洞开,各种与春有关的作物纷纷登场,真个是万物并作啊!春茶自然不甘落后。
“雀舌”是新茶的雅称,刚绽芽的茶叶尖,非常形象。茶的雅称很多,还有乳茗、先春、金叶、仙芽、云腴、碧霞、云华、瑞草魁等等。看到这些名字,茶的美好形象便浮现在眼前了。不过坦率而言,在东白山老家时,根本没有这么多诗情画意,对茶的印象,最多的是“大碗茶”和“口渴茶”。我们喝的,基本上是“大茶叶瓣”,不是“雀舌”,而是茶叶到了“伸手伸脚”时候采制的茶叶。那时,“谷雨先茶”已经属于比较早的了,现在则采摘期越来越提前,似乎茶芽越小越金贵,味道越好。我对茶没有研究,但对此是颇不以为然的,以为茶叶还是需要适当有点“成熟期”,味道才浓烈,否则,淡淡的,喝的只是一个概念。我当农民时喝的茶叶比较“成熟”,有两个原因,一是采摘期早一些的茶叶,都是卖给公家的茶厂,卖给供销社的;二是农村里的人整天干苦力,出大汗,哪里有心思品茶?喝的大都是泡的浓浓的“大碗茶”,越浓,越苦,越过瘾。特别是夏天,出门干活,人人都带一个“排竹罐”,放进大把的大茶叶,灌进好多开水,就这样浸泡着,休息时,仰起脖子,猛灌一通,真正的牛饮。有时光浓茶还不过瘾,要放一些“消饭花”“阿药草”之类的草药,解暑、清凉,有人难得吃了橘子,那皮都是舍不得扔的,有人也喜欢泡一点到茶里,添几缕香气。家里也没有每人一只茶杯的习惯,用一只陶瓷做的大茶壶,或者大钵头,一早就泡上满满的一壶、一钵头,文雅一点,用小茶缸舀出来喝,干农活回家渴极了,就端起茶壶、茶钵头,仰天便饮,可以一口气喝干,旁边的人清楚地听到喉结滑动的声音,“咕咚咕咚”,这滋味,与喝酒可以一比。这样的喝法,放几片“雀舌”,会有感觉吗?
陆羽《茶经》对“茶”的解释是:“其字或从草,或从木,或草木并。其名,一曰茶,二曰槚,三曰蔎,四曰茗,五曰荈。”故乡的“大茶叶瓣”,大概属于“荈”的范畴了。荈,指茶的老叶,即粗茶,后泛指茶。俗话说“美酒不如粗茶数盏”,其实酒和茶并不矛盾,应该可以兼而并得。唐代诗人施肩吾有诗云:“茶为涤烦子,酒为忘忧君。”两者的功效,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不过这也说明,“粗茶”的价值,是被人低估的,许多一辈子喝嫩嫩的“雀舌”而不喝粗茶的人,很可能并没有真正领略到茶的至味。
故乡的凉亭,比如东前岭的凉亭,都有“施茶”,放一只大木桶,旁边挂几只毛竹杯,泡一桶浓茶,一般都会放一些“消饭花”,供过路人免费饮用。有时还会有“施草鞋”的,好心人做几双草鞋挂在墙上,如果“脚力”路过,恰好草鞋破了,就换一双,事情虽小,也是一份实实在在的功德。“十里一长亭,五里一短亭”的诗意景观,在现代社会早已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高速公路“服务区”,在那里一切都转化为商业模式,“施茶”“施草鞋”自然成为天方夜谭了。
我的老家斯宅有过几家茶厂,一家在“新祠堂”,也即“华国公别墅”,那里曾经是竹器厂,也是茶厂,村民们采了茶叶,就卖到那里去。有意思的是,茶厂的前身,也是茶厂。年,就建了“永义茶厂”,到了年,改名为源大茶厂,继而改为大生精制茶厂,居然开始做外销茶,远销美国和俄罗斯等国家。到了年,茶厂收归集体所有,由同族的斯根坤负责管理。令人称奇的是,斯根坤97岁高寿了,已经成为斯宅红茶的非物质遗产传承人,直到现在,身体健康,还会亲自制茶。我之所以写这篇文章,也是在看到斯根坤先生的孙子小锋不久前发了斯根坤先生在制作“百年红”红茶的照片后,心有所动,觉得应该写写故乡的茶,才开始动笔的。斯根坤先生和斯孝坤先生是昆仲,哦,论字递,我和他们平辈,遇到了只要称阿哥即可,但我见到孝坤先生,还是以“先生”相称,毕竟“辈大不如年长”啊!根坤先生多年未见了,下次回故乡,应该专门看看他,和他品茶论道。
在“人民公社”大集体的时候,斯宅还办过一家规模不小的精制茶厂,厂址就在现在的“十里红妆”博物馆。那里原本是一家“发电厂”,供应村子里的照明用电,一个晚上供应几个小时。要熄灯时,一关一开打三次“招呼”,然后便停止供电。记得不是哪一年开始有电灯的,但清楚地记得电灯开通时的喜悦之情。“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就是“共产主义”生活,这样美好的“共产主义”生活就少一部电话了,尽管祖传的楼房是破旧的,电灯一个晚上只亮两三个小时。
今年97岁高龄的“老茶农”斯根坤先生(左)
后来公社在这里办精制茶厂,斯宅大队的支部书记友文和王坑大队的支部书记洪兴两员大将抽来负责,一度办得红红火火,可惜后来因为种种原因停办了。精制茶厂的掺着茉莉花的珠茶,我也是品尝过的,味道现在仿佛还在舌尖。洪兴书记早已作古,友文叔八十多了,身体仍很健康,天天上山、下地干活。
斯宅曾经流行过一个叫“石笕茶”的茶叶品牌,有好几年,“石笕茶”是馈赠佳品,机关部门的头头脑脑喝的都是“石笕茶”。流行了十多年,也就慢慢衰落了,衰落的主要原因是没有“龙头企业”来引领,没有研制机构和质量保证体系,千家万户分头制作,用相同的包装袋包装,真假难辨,渐渐地就砸了牌子。不过,直到现在,我依然非常怀念当年的“石笕茶”,怀念它的质朴自然,原汁原味。
现在的故乡东白山,已经有了一家颇具规模的越红茶业,以及配套的越红茶叶博物馆、越红茶庄等,把茶叶“非遗”做得风生水起。
茶有久远的历史,传说中神农尝百草而时有中毒,常以茶解之。也有佛门闲人或为扩大佛教影响计,而宣扬茶是随着佛教自东汉由西域传入中国而传入的。饮茶的习惯,初盛于寺庙,僧人坐禅,茶为驱睡之物。南北朝时,饮茶开始由寺庙传播至贵族士大夫,然后至文人,茶文化开始逐渐萌芽。到了唐宋,茶文化已经发展至鼎峰。陆羽之所以成为“茶圣”,与他从小被方丈收养,习茶启蒙于寺庙,不无关系。更何况陆羽的“指导老师”皎然就是著名的“诗僧”,皎然是真正的“茶禅”的祖师爷。
喝茶提神明性,有助于消除疲劳,驱赶瞌睡虫,故有“不夜侯”的美称。典出西晋张华《博物志》,云:“饮真茶,令人少眠,故茶美称不夜侯,美其功也”。自从参加工作以来,便养成了“清茶一杯”的习惯,到了办公室,第一件事便是打开水,或者烧开水,而后泡一杯茶,开始伏案办公。如果出去开会,或下乡,也是一杯在手,不管到哪里都可以喝。喝茶,是机关干部的“标配”,与当农民时喝“大茶壶茶”相比,这样一杯清茶的办公生涯,不啻于神仙过的日子了。如果要熬夜赶材料,或者自己搞文艺创作,更是少不了一杯好茶相伴。
这幅书法写于今天
这样与茶相伴的日子,一晃就几十年。退休之后,喝茶更加成为每日的“必修课”了。我喜欢喝茶,但对茶并无多少讲究,有什么茶就喝什么。一般而言,早晨起床后先喝一杯温开水,而后泡一杯龙井、安吉白茶、东白野生茶等绿茶,有时早饭前就开喝,中午之后,转为喝老白茶、陈年普洱或红茶、黑茶,晚上则喝得淡一点,临睡前喝一小杯温白水。一家人都爱喝茶,一天下来,“茶叶渣”不少,想到采茶工、制茶工的辛苦,感到倒掉了也可惜,有时会积起来烧茶叶蛋,做到“物尽其用”,不浪费。我始终觉得,所谓“惜福”,就是尽量不浪费,更不暴殄天物。现在的绿茶都是“雀舌”,太淡,不适宜烧茶叶蛋,与老白茶、普洱、黑茶的茶渣掺合在一起,再放一点咸菜,是不错的选择。
三、与石俱焚毛洪涛---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10月18日上午,成都北郊殡仪馆,告别大厅四周摆满了花圈,正中挂着一幅遗像,上方打出字幕:沉痛悼念毛洪涛同志。上午10时,成都大学党委书记毛洪涛遗体告别仪式在这里举行。毛洪涛的亲属、生前好友、同事、学生等近千人来到现场,参加遗体告别仪式。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在现场看到,从早晨8点开始,已经有不少人陆续来到现场。9点左右,毛洪涛妻子在别人搀扶下缓慢步入现场。毛洪涛生前众多学生及同事手捧菊花,列队入场,神情哀恸。有不少班级或学生以个人名义送来花圈,挽联上写着:“痛失恩师”。
在现场,记者并未看到成都大学校长王清远出席,记者多次拨打王清远的手机,提示关机。
四川排名第一的会计学专家
10月15日,毛洪涛在朋友圈发布了一条带有“绝笔信”意味的长文后投河溺亡,迅速引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