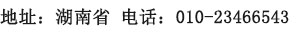市场营销求职招聘交流QQ群 https://m.sojk.net/yinshijj/26323.html
撰稿张世华(主笔)郑超英(协助)
织女桥东河沿位于天安门以西百余米的南长街内。走进南长街大拱门几步,东拐至中山公园红墙,往北几百米,再向西至出口的C型胡同,便是织女桥东河沿。这条胡同的初始形成,要追溯到明代。据道光、咸丰以来的朝野杂记中记载:故宫西华门外以南只有南府乐部和杂役人居住,并无路可通,皇城南墙天安门东西两端,亦没有出口,只是到了民国三、四年,南长街才开建,开辟街门之前,皇城南墙内的南段路西,称为南花园。根据明朝嘉靖三十九年《京师坊巷志稿》记载:“明朝时,南花园在西华门迤南东向,称为灰池,(指如今紧邻南长街东侧的中山公园一带),春季在坑洞内烘养春季蔬菜供咬春,夏季培育各种江南引进的花草盆景分时送入宫内,秋季收养蟋蟀,正月十五戏赏鳌山灯会。”通过这些描述,可以想见明清时皇城西侧无论作为皇宫建设的施工灰池,还是后来做为皇宫生活娱乐的服务供给都是一派生机勃勃,物盈丰盛的景象。资料显示,中山公园年建园,南长街开辟于民国三、四年(、年),两座同期建立。据此分析,织女桥东河沿胡同便是依中山公园建园与南长街的开辟,由原杂居在这一带的皇宫杂役人家为起始,后经中、外不同背景的人们先后来到这里建房、盖楼,而逐渐形成的。织女桥位于南长街一直往北约米处,与织女桥东河沿胡同的西北出口纵横相邻。据史料记载,织女桥始建于明代,年6月改建,为单孔石拱桥,桥长17.2米,桥宽17.6米,南北走向,汉白玉雕花栏杆,桥面由花岗岩条石合缝拼接。此桥一直存留并使用到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后期。五、六十年代,汽车较少,红色、外形如面包、捷克产的5路汽车是来往于南、北长街上的仅有的一趟公共汽车。每当车辆驶过石板桥,总能听到"杠、杠“的回响,与在柏油路面上发出的声音不一样,所以印象挺深。织女桥下的河水由中南海的东墙流水涧下的水闸流出,沿小桥北河沿约百米露天河道,流入织女桥桥洞,继而进入中山公园红墙下的水箅子,流进公园里。这段露天河道风景别致:河两边是自然山石块,有的花岗岩石面如洗衣板,上面呈现一条条的勾槽,想必是前人为洗涮之用而刀凿出来的。小时候,我们常从家里拿着木棒锤、皂角或碱面,来这儿洗衣裳、玩儿。水边不深,清澈得能见小石子,每每能见到细小的游鱼有水中嬉戏,倏忽不见,再也难寻踪影。小河靠近中南海外墙的那边,还有一座由6至8根树桩支起,桥面由长短不一的木板搭建的小桥,供居住在小桥北河沿西边与南岸小胡同里的人们穿行之用。河的南岸有南长街小学院墙里恣意生长出的高大老桑树,枝叶伸张,茂密如棚,遮阳庇荫在小河上方,桑椹成熟时,常悉数落入水中,伸手去抓,捕到水面,顺水流跑了,捉不到,一身湿,充满了乐趣。还能记得每逢农历七月十五祭祀故人,奶奶满是肃穆的表情,带着不敢出声的我们,将用秫秸杆做支架、高粱纸糊的河灯,放到河水中,顺流而去的景象。当夏日汛期来临,中南海开闸放水时,常有大鱼卡在中山公园墙下的水箅子处,爷爷擎起大石头砸中大鱼,之后下到水中,用大手攥住活蹦乱跳的大鱼的情景,还浮现在眼前。大概五十年代中后期,不知何故,织女桥被拆掉了,小河改为地下管道,地面上盖起了一个制作铁夹子的街道工厂。再后来,中南海的东墙外扩至南长街路西的马路边,这里就变成通往中南海侧门的一条通道,临街有军人站岗。八十年代中后期,中南海曾经部分地开放,人们持票就从这里进入,去参观毛主席居住过的丰泽园和菊香书屋。织女桥东河沿胡同里的往事,至今我们还有记忆。从胡同北端的1号院计起,至南端的南花园18号是全胡同总门牌数。其中,6号与10号院中的小洋楼最有特色,极具建筑美学价值。之后,我们再也没能从视力所及的国内外任何地方或资料里,看到过与这两幢小楼相似的建筑!6号院中的小洋楼是座外饰为红白色相间的3层楼房,长与宽都近20来米,从地下室起至1层底座是黄沙色的花岗岩,1层至3层为红砖砌成,屋顶由青色石板一层层铺叠,在屋檐与楼垂直折角处有灰色铁皮排水管道,楼的西侧墙与3号院相邻,南、东、北面则是6号院的院落,外围有数间为配套使用的平房。一进院,往右是丛大丁香树、大榆树;往左拐的南面是几棵高大的洋槐和榆树、桑树,这些都是有年头的老树。院内外的孩子们都是从它们开始认知这几种树的特征的。从有关资料获知,清末民初,北京城曾兴建了一批西式洋楼,据说这座楼就是那时由德国人设计建造的(胡同中的11号与18号楼也均属西洋式楼房)。著名的那张年8月18日毛主席戴着红袖章在天安门城楼西南角挥手的照片,主席胳膊肘下就是6号楼,后来发表的照片,修版后用绿色给遮盖了。这座楼的3层东南侧是一个10多平米的大露台,记得那时,楼里院外的小孩都喜欢聚在这里,春末夏初,槐花香满枝头,我们伸手够着槐花,边吃边玩;摘桑叶,养蚕,直到见蚕吐丝成茧;养鸽子、放鸽子,听鸽子咕咕叫,看着成群的鸽子在屋顶上兜风般地盘旋!置身其中,感受着人与动、植物间的和谐美好共生!每逢五一、十一的夜晚,大家围坐在露台上,共同欣赏天安门广场上腾起、绽放礼花的盛景。过后,兴趣盎然地在树梢寻找礼花燃放后掉下来的小降落伞,下楼去到胡同里寻找撒落下的没有燃烧尽的礼花炮。找个晚上,我们再凑到一起燃放捡来的礼花头,那被火光映照的脸庞和兴奋的喊叫声,此时又在脑海里闪现。礼花掉下来的碎渣里有棉籽,7号院的墙根处隔年就长出过棉花棵子来,还结出了饱满的棉桃呢!胆子大些的孩子还会爬到青石板铺盖的尖尖的楼顶,在那里眺望天安门、中山公园,绿树红墙,汉白玉门柱,青、红、白、黑四色琉璃瓦围墙的五色土社稷坛,以及更大面积的、层层叠叠的、金黄色的故宫大殿琉璃瓦,夕阳下异彩纷呈,熠熠生辉。据说,旧时的6号医院。从地下室至地面3层,楼内绛红色的木地板,地脚线以上1米至是蓝色漆成的腰线、米黄色的门窗和纺锥花瓶造型的楼梯扶手、壁炉等一派欧式风格。2与3层的楼梯拐角处还有一斜顶的房间,是旧时佣人的房间。楼顶有几个直通壁炉的耸起的砖砌烟囱,楼的1层至3层露台的东南相交处呈东南向侧角,从上空俯视,其楼顶是南北与东西两个尖顶相交。整个楼从外部看上去高低错落有致。听老人们讲,这座楼在解放后迎来第一拨的新主人是穿着灰色解放服的人们。后来先后成为全国总工会,农机部的干部宿舍,院里住有六户左右人家。五十年代,每到暑期,此院中的孩子戴着遮阳帽、穿着皮凉鞋,叽叽喳喳地在门口等机关来的汽车接送他们去北戴河度假,这让其它邻居们的小孩子很是羡慕。这座小洋楼于年因修建国家重要工程随之被拆。同期,织女桥东河沿胡同原1至9号不复存在。前不久从网上看到美国生活周刊刊登年的一张航拍照片,有6号楼和10号楼、11号楼的珍贵远景图。截图于此。由北向南依次为6号楼,10号楼、11号楼。隔过7号至9号或破旧或完好的平房院后,就是10号院的一座暗褐色,全部是耐火砖的2层小楼。大门是拱形顶,红漆。大门往北是楼的1层,往南有10米长的高高围墙,围墙每隔两米左右建有突出的砖砌方形柱子,顶上有带铁罩的洋式路灯。我们曾有幸进去过几次,从门口进入左侧便是几层台阶,一棵细高的枣树,往西约20米,往南约10米是个长方形的大花园,里面种有蝴蝶花、鸡冠花、美人蕉等各类花卉。站在花园往北看这座楼,楼体从西起至东,有一半多长是个敞开式露天无围栏的露台。从楼里走上露台,看到上面是由四方红地砖铺就,说是用来跳舞的舞池。舞池下面的1层与半地下是通体的透明玻璃墙,进入半地下的室内,墙边放有一棵缀了许多糖果和彩色小玩意的大圣诞树。横亘东西的一个下凹式大水池里,竖有一个喷水的、有半人高、郁郁葱葱、长满青苔的大上水石的假山,上面点缀了许多的楼榭、廊桥、亭台、庙宇等微缩、彩瓷、古典的小景观!喷水溅出的水雾,在宽大玻璃窗投射进来的阳光下,时而氤氲,时而彩虹。红色大尾鱼在水中游弋,充满了意趣。小孩子见到这景儿,如同走进了神话世界,被吸引得根本就不想挪窝儿了。这幢小楼的主人是民国次外长曹汝霖第四个女儿,老邻居都称她为曹四小姐,她终生未嫁,至年生病去世前一直住在这里,后来她的骨灰被送往了台湾。因在女主人生前,我的奶奶曾给她家做帮工,得到其信赖,曾送给过我家一座镜台、一盒精致的麻将牌、两盆腊梅花、佛手花及绣花鞋面等物。现在家里仅存的只有那个镜台了。{配照片}之后,这里归国家所有。这里,先是住过一家匈牙利人,他们与周围邻居相处得很是融洽。那时,午饭后我们2、3个小孩常在10号门口喊;“冰激凌、冰激凌!”男主人就会出来,用手轻拧一下我们脸蛋,然后发给每个孩子一毛钱。周末,还能坐着他家小汽车去接寄宿学校的两个孩子。记得这家的外国大男孩看我们吃蒸熟的榆钱拌玉米面后,他便爬上墙,从院里的大榆树上,撸下几串榆钱儿,打了好几个生鸡蛋,在把儿缸子里搅和着那么吃!后来,是乒乓球国手容国团在此居住。从没见过有汽车来接送这位长得非常帅的世界冠军,倒是偶尔能见到容的妻子穿着颇为少见的桔红色的确良上衣,高个子、白皮肤,挺丰腴,站在胡同口等着。每逢他们夫妇从胡同里走过,没有出现过追踪、围观的人。再后来,就成为捷克斯洛伐克驻京海运办事处,门外加了警察站岗。年10号楼未被拆,直到年左右还在,但胡同里的那排大树全没了。近几年再去看,10号楼的位置已被一座灰色高墙、装有电网的新贵的宅子取代了。五、六十年代,生活普遍不富裕,民风也淳朴。干部家庭生活与平民家庭的差距不太大。我母亲工作单位在地安门后门桥附近,每天要走着往返十四、五里路去上斑。6号楼里住的广东籍的延安时期老干部郑局长夫妇,大多时候也是来回步行十多里路,去位于沙滩大街以东的八机部。偶见有小汽车来接送时,也是带上别的干部。又比如,住在北长街前宅胡同的同学的妈妈,为照顾好孩子们的午饭,好长一段时间都是走着到西单以西的水产部,这也是十多里的路程,要说,这可是位有着革命资历的机关干部、局长夫人!还有住在西华门以南、路西大绿门里的瞿秋白夫人杨之华女士,也是常能见到她步行到全国妇联去上班。那时,织女桥东河沿胡同里更多的是平房住户。我家就分别租住过7号与4号平房,老租户与房东的关系都还不错。记得住7号院平顶南房,下雨漏水,屋里接着4、5个盆,外面下大雨,屋里滴滴嗒嗒下小雨的情景。天晴了,自己动手修补。奶奶找来沥清块,让我在火炉里拿出烧红的铁通条,登梯子递给她,她用来融化沥清,补房顶的漏地儿。7号的院墙长年坍塌一半,是全胡同最残破的一处。租住南房的我们一家,几个孩子每晚盼望父亲下班,抬起自行车前把,转动车轮,显示磨电灯随轮速的快、慢,由亮变暗灭的过程,引发我们的好奇和求知欲;之后,又期望获得他偶尔能从上衣兜掏出个“糖耳朵”,每人给掰一口吃的欢喜!后来,爷爷独居这间没电灯的屋,我和姐姐晚上去时,就在墙上拴了根浸了煤油的纸绳,点燃取亮儿。当见到爷爷用破筐压在脚底下的破被上御寒睡觉时,心里不好受又没办法!夏天热,屋窄,我们常露宿在院子或胡同里的院门口,躺在破木条钉起的长方形大排子上,奶奶搧扇驱蚊,我们仰望夜空,指认牛郎、织女、北斗七星的场面,那是一幅实际版的丰子凯画作。每逢五一、十一节日,孩子们纷纷拿着向日葵的长杆,去树上够放礼花掉下来的降落伞,那可是这条胡同独有的热闹景象:一阵璀璨的礼花过后,天空便出现一串串由彩色小降落伞吊着的礼花壳,这些随风飘落下的小降落伞,多数落在这条胡同的一些大树枝上,大人、孩子们就随风向而追,一次追进院子里把火炉上的壶水都撞翻了!记得在10号门口我们还捡到过掉下来的大气球和长幅红布标语!胡同里大概有两、三户人家,利用节日人多,烧茶水到南长街出口以东,长安街的北便道边上去卖,二分钱一碗,听母亲讲,三天能挣三、四十元,对生活可起了大作用。那时年龄虽小,但也是卖力气地去推着小车送水、放板凳、摆摊;我们还常去胡同南口的南花园,因那里是中山公园与人民大会堂倾倒燃煤炉灰的地儿,拿着用粗铁丝做的爪篱和破筛子去捡煤核儿,补贴家用。胡同靠中山公园红墙一侧是一溜儿大槐树,另一侧是住户。小河、红墙、绿树、民居的布局,使得这条胡同的生态和谐、空气清爽、整洁又静谧。夏天,胡同里的男孩子们用旧车胎熬胶粘“知了”,雨后,用大扫帚捕打成群的低空萦绕的蜻蜓,之后把逮住的夹在手指缝间;女孩子们则拿着空墨水瓶,顺着胡同两侧的墙根去捡槐树虫,挖蛹。见到吊在半空中的槐树虫,就一边跺脚,一边喊“嘟!嘟!”虫子就会掉下来,装瓶回家去喂鸡;挖出紫色外壳的虫蛹,手捏着它,嘴里嘟囔“金刚、金刚转转,姆们、姆们看看!”虫蛹就会扭动头部,绕圈转悠,那叫一个逗人!把虫蛹的本能反映,附加了人、虫互动的乐趣!冬天,西北风呼啸,风力和声响很大,风后胡同里会出现一地的干树枝,出去一趟就能捡回一大抱,在7号院东墙下奶奶垒起的大柴锅的灶里当柴烧,锅里熬粥,四边贴玉米面饼子的饭食,那可真是香得很!还记得一次,姐姐往灶里扔进个未燃的花炮头儿,一下子炸响,把在灶前烧柴禾的爷爷,吓得摔了个后仰脖儿脚的大屁蹲儿!幸好没把柴锅炸裂!胡同里靠公园墙处,常堆放着大堆的煤矸石,常能从中发现镶嵌着指甲盖大小、方型、酷似黄金及色泽,俗称“自然铜”的煤矸石。直到如今,受知识面所限,也没能搞清这是什么矿物质?在放置能达公园墙高的、建筑脚手架用的杉槁堆上,孩子们常爬上去翻墙进公园玩,这样能省下门票钱。墙内至少有2米多高,女孩子怕摔坏崴了脚,就紧贴着墙跳,这样能加大摩擦力,下去的速度慢些。记得一次,我这样跳进去后,可能是戳了尾骨,姿势象蛤蟆样,贴墙站不起来了,好一会儿,才缓过劲儿站起来!墙里是只有1米多宽的土路,接着就是斜坡,再下面是通往金水桥的小河,墙外边的大孩子怕里面的掉河里,见跳进墙去一个,就喊一个名子,里面的怕被公园管理人员听见,只得小声儿应答。真叫默契!暑期的每个周末,公园都举办“电影晚会”,即使隔着一堵墙,公园内的欢乐也一样感染并吸引着墙外的孩子们!园内举办活动播放的乐曲,同样在胡同里回响,喜洋洋、步步高、紫竹调、金蛇狂舞、春之声圆舞曲、多瑙河之波等等太多的中外名曲的旋律,孩子们大都能哼唱!如今,从这条胡同走出的孩子,有的已成为获得国家级奖项的影视导演,有的是进入国家顶级乐团的音乐人才,更多的则是分布在各领域辛勤劳作的普通一员,但大多都有着对音乐与艺术的爱好。一个世纪的风云际会,如今没了树木的半截胡同仅存!那深藏于心底的亦古朴、且乡土、亦市井、又高贵的曾经的织女桥东河沿胡同,永远是我们心中最祥和、宜居的地方。阅读往期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