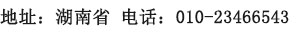本文大概字阅读需要8分钟我把朱鹮看作是生命,而不是鸟。在我的童年记忆里,有两种动物曾经濒临绝境,命悬一线。一种是国宝熊猫。不过现在的种群数量之多,已经从濒危红榜里光荣隐退了,这是极其了不起的成就。另一种也是国宝。只不过它们不仅仅是中国的国宝,更是东面岛国的国宝。它们的命运,就没有卖萌求生的黑白汤圆那般外挂式否极泰来了。真正的日本国鸟,朱鹮(学名:Nipponianippon)是鹮科朱鹮属动物。中国古称朱鹭、红朱鹭,系东亚特有种。中等体型,体羽白色,后枕部有长的柳叶形羽冠,额至面颊部皮肤裸露,呈鲜红色;繁殖期时用喙不断啄取从颈部肌肉中分泌的灰色素,涂抹到头部、颈部、上背和两翅羽毛上,使其变成灰黑色。这种姿态优美,毛色秀丽的鸟类栖息于海拔-米的疏林地带,,漫步觅食小鱼、蟹、蛙、螺等水生动物,兼食昆虫;在高大的树木上休息及夜宿。朱鹮是留鸟,秋、冬季成小群向低山及平原作小范围游荡;4-5月开始筑巢,每年繁殖一窝,每窝产卵2-4枚,由双亲孵化及育雏,孵化期约30天,40天离巢,性成熟为3岁,寿命最长的记录为37年。曾广泛分布于日本、中国东部、俄罗斯、朝鲜等地,由于环境恶化等因素导致种群数量急剧下降。以至于上世纪末在日本全境灭绝,仅中国陕西省洋县秦岭南麓有唯一7只野生种群,其危急程度甚至超过了熊猫。后经人工繁殖并野外放养,种群数量逐步恢复。日本国内的种群,经过中日两国人民、领袖以及生物学家的共同努力,由中国种东渡扶桑,也开始逐步恢复。这是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当世界改变的速率快于物种适应的速率时,这些物种大多会崩溃。获得年普利策非虚构类写作奖的伊丽莎白·科尔伯特在她的《大灭绝时代》里曾经总结到,地球在历史上曾经有过5次生物大灭绝。宇宙变动、自然天灾,每一次,地球都会失去一些生物;每一次,也总会有新的物种诞生繁衍。地球生命在漫长的时间里相安无事、演化渐变,但是,地球现在进入的第六次生物大灭绝时期与以往大有不同。这一次的生物大灭绝由人类引发,人类成为了主宰生物世界的角色。仅仅过去的30年,就有上百万种生命形式灭绝。生物多样性的危机因而受到注意,并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核心议题。具有强烈自省意识的日本人不会放过这个检讨的机会。年出生于日本长野市,一向以环保相关内容著称,先后写就《丝虫——誓要根除难治之症的人们的记录》、《绘神之人——田中一村》、《死贝》、《害虫歼灭工厂》、《姬百合:来自冲绳的信息》以及《梦之箱:被杀死的宠物》等纪实类作品的小林照幸,于年出版《朱鹮的遗言》一书,回望了日本野生朱鹮灭绝前的几十年历史,向读者们完整呈现了这一物种凋零的过程,随后获得日本大宅壮一非虚构文学奖。这是一部通过濒临灭绝的鸟类朱鹮,向人们展现人类对自然所犯的罪,以及想要偿还罪行的人类如何苦战、挣扎的报告文学。——柳田邦男(日本著名非虚构作家)Nipponianippon,朱鹮的学名象征着日本。古时候,日本人就将朱鹮当作圣鸟。朱鹮展翅飞翔时,阳光下的羽翼是淡淡的粉红色,被称为“朱鹮色”。它们的羽毛是优雅而尊贵的装饰品,甚至出现在伊势神宫重要的迁宫仪式上。这种美丽的鸟,曾经遍布日本全境,到年代,只剩新潟县的佐渡还观测到它们的踪迹,但已经数量不足百只。将自己的命运和朱鹮紧紧捆绑在一起的佐藤春雄经年累月地对这个物种进行观察和保护。在他眼里,日本的朱鹮每十年会迎来一次大的变化。昭和初年,日本政府将朱鹮指定为“天然纪念物”;昭和一十年代,朱鹮因战争而被人们淡忘;昭和二十年代,佐渡朱鹮爱护会为代表的保护组织成立,朱鹮重回人们视野。平成七年,换算成昭和的话,应该正值昭和七十年,最后一代日本本土朱鹮产卵成功,但留下的五颗卵全部孵化失败,日本产朱鹮彻底灭绝。《朱鹮的遗言》记录了佐藤春雄、宇治金太郎、高野高治等爱鸟人士,如何不遗余力地保护最后的朱鹮。以及这些最后的幸存者是如何一只一只离世,留下人们无尽的遗憾和懊悔。佐藤春雄本是高中老师,只要有空就去观鸟。只要当天见到了朱鹮,便喜悦无比,连学生们都拿这件事打趣。他记录朱鹮的习性,破解了“黑白朱鹮”之谜;他收集朱鹮的粪便,把家里搞得臭气熏天,也由此建立了最翔实的一手生物学资料。宇治金太郎是野生朱鹮最亲近的人类,谨慎的野生鸟儿只有在他身旁才会旁若无人地自由进食甚至投入人类的怀抱。高野高治住在深山里,从小与朱鹮为邻。长大后他也没有离开深山,冬日大雪封山,为朱鹮投食成了他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这些人并非动物学家,更没有从保护朱鹮的事项中得到任何物质回报,反倒还要倒贴大量金钱、时间和精力。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当然,作为佐渡本地居民,发自内心地喜爱特有动物是他们淳朴的动机。更为重要的是,他们不忍心放任一个物种与这个世界永别。这也是大部分投身于动物保护运动之人的共识。在《朱鹮的遗言》中,有一个问题被反复提及:既然朱鹮这种鸟对环境如此敏感又如此脆弱,是不是应该遵从物竞天择的原则,放任其灭绝?佐藤春雄却毫不犹豫地回答:我把朱鹮看作是生命,而不是鸟。人命是命,朱鹮的命也是命。如果因为横竖都是一死,便置之不理,那人也不需要医疗、福利了。可是,人与人之间,对待病人,我们必定是要帮助,是要安慰的。本书作者在听到春雄的回答后,不由得提出振聋发聩的疑问:一个物种在日本灭绝,与其追责,不如反思,对生命的慈爱是如何从现代日本消失的?这个问题,也值得问现代社会的每一个人。《朱鹮的遗言》还从技术的角度,深入探讨了关于环境和动物保护的若干切实问题。对于濒危物种,人类到底该怎么保护?战后的日本政府虽然对朱鹮的处境一清二楚,但国家和地方层面都没有足够重视。说起保护点头称是,讲起落实束手无策。无资金无人员无政策让民间保护者们无所适从。朱鹮保护者与农民、猎人、旅游开发者之间的矛盾也一直存在。朱鹮栖居树上,在树上筑巢,茂密的枝叶能够遮挡它们的踪迹。可是,森林砍伐毁掉了它们的家园,鸟巢安全度和私密性的降低,让鸟卵和雏鸟都无法拥有可靠的亲代保护。朱鹮由原来自由自在地亲近人类变得极度警惕人类的接近。另外,现代农业大量使用农药,让在水田环境中摄取食物的朱鹮经常陷入危机。它们要么被毒死,要么被饿死。此外,朱鹮有时还会误踏猎套,或被台风、暴雪等恶劣气候吹入迷途。走投无路的日本人,选择了人工圈养这种方法来保护最后几只朱鹮。他们花大力气将仅存的鸟儿全部捉住,天天好吃好喝喂养着。可是这种方法就有效么?在《朱鹮的遗言》里,答案并非如此。人工饲养的狭小空间压抑了鸟儿的天性,加之人类对朱鹮的主动认识开始得太晚,掌握的知识有限,任何一点失误都将它们推向悬崖之下。日本的案例表明,人工养殖陡然加速了野生朱鹮的死亡,捕捉则进一步破坏了朱鹮的生活环境,迫使野生朱鹮不停地迁徙。相反,中国对野生朱鹮的保护采取了另一种方式:大面积划分保护区、严禁使用农药、严禁捕猎和下套、尽可能给鸟类一个自由生长的环境,依靠生物自身的力量来恢复种群。人类是环境的破坏者,现在将破坏的环境恢复起来,生物自有其发展之道。截至年,中国野生朱鹮的数量已经回升到了只,总数达只。朱鹮成为除熊猫之外,另一位深受人们喜爱的动物外交官。通过向日本赠送朱鹮种鸟,中国帮助日本重新建立了朱鹮种群,如今日本的朱鹮总数也已稳定在了只左右。这是中日合作的典范,也是世界动物保护史上的成功范例。事实证明,社会主义中国的举措更科学、更高效、更有利于野生动物的保护。熊猫保护的过程,为中国方案增加了更多的说服力。这一点,也让日本的保护者们钦佩不已。有意思的是,译文出版社前几年出版了《最后的熊猫》一书,与《朱鹮的遗言》堪称姐妹篇。自然与人应该和谐共生,自然与人能够和谐共生。前弹推荐:《老谋深算的一秒钟》
这是读影发作第篇
一个粗人,读些书看些电影
写些自以为是的东西
如果喜欢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