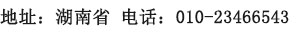一九六二年初夏的一天清晨,西蜀山土地庙前的小河埠头上泊着一条木船。船尾坐着一个中年妇女和五六个小孩,船舱里几个包裹和箱子就是这一家人的家当。他们要去的地方很远,用双橹摇恐怕也得走一天吧。这个中年妇女就是我的母亲,她是一个教师。
半年前,文教局把她从王庄调到这个山脚下的土地庙教书,不知道是没有学生来上课还是其它什么原因,这个设在土地庙的学校就停办了。
那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教育局领导按照母亲的要求把她调到沙地片去。母亲要到沙地片去,出于抚养她的五六个子女。那个年代的萧山,沙地似乎更适合人们的生存,尤其是拖儿带女的母亲。自从4年前父亲失去工作流放到牛头山,养家糊口的担子就落到了母亲肩上。
(之江夕照——廿几年前在围垦五工段拍摄)
摇橹的是西蜀山的两个小伙子,记得一个叫“大脚阿兴”,他的一个小腿患丝虫病;一个叫“乌毛”,黑黑的脸。萧山的沙地沿钱塘江,从西到东横跨萧山县域数十华里。调母亲去教书的地方在一直东面,当地人称东沙。由于是穷乡僻壤,交通困难,很少有教师愿意往那个地方去工作。
从西蜀山到东沙水路有近华里。过了响午,船到了航坞山下的塘头闸。这个闸是里坂与沙地的交界处,船出了闸就进入了沙地区块。闸外面的河不再是叫河,叫作“湾”,出了闸有纤路了就可以拉纤了。我们上岸在塘头闸上稍事停留,船工要准备纤绳纤板。“五香盐精豆,大昌好酱油,东街吃到西街头,揸屁揸到闸高头”我被在闸上做买卖的吆喝声所吸引。一带乌毡帽的中年汉子,守在一副担子前,担子上有一转盘,转盘上布了几根纸条,上面写着50//,对着转盘有一飞镖装置,在转盘转的时候,扣下击发开关,飞镖飞向转盘,一分钱来一下。我看了几个人,飞镖击中大多是50,因为、的纸条很窄。这盐精豆是当地的罗汉豆烧煮,用甘草,五香粉调制,闻着很香。我没有一分钱,要不然也会来一下的。
出了闸是一个船码头。码头上歇着几艘航船,几条埠船。沙地的交通,那时候除了独轮的“羊腿车”就是船,再就是步行了。到我们要去的地方有机航船,三条船栓在一起,前面一条船上有一台挂桨机,据说一天只有一班。埠船有橹摇的也有用撑杆舭的,一根长长的撑杆舭在船尾,人在岸上一边推着走一边“堂堂堂”敲锣吆喝。湾的两边的河坡上长满了芦苇和茅草,背纤的人如果不用力,纤绳就会被被芦苇缠住。两个船工一个人摇橹,一个人背纤。为了早一点赶到目的地,我也上岸背纤,此时的船明显快多了。
木船在湾里行驶,每当迎面有船过来,背纤的人要钻过对面的纤绳,而对面背纤的人则要把纤绳晾过我们船上的桅头,这样才不会使双方的纤绳交织在一起。好在来来往往的船不是很多,要不也挺烦人的。
在木船过了甘露庵的时候,看到湾里有两条水牛一前一后分别拖着长长的一溜木船迎面而来。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牛拖着船在水里行进的,此前我只知道牛拉车。后来当地人告诉我,这种用一头水牛拖上五六条木船的就是牛拖船,是沙地特有的一种运输工具。沙地的湾由于土质是沙泥的关系,一下雨湾两边的土就被雨水冲刷到湾里。要不是湾边长的芦苇护坡,挡住沙土的淤积,船就不能在湾里行驶。牛拖船的构造也与一般木船不一样,船底是平的吃水不是很深,装载的货也不少很多,也就是三五吨。
有了两个人在岸上背纤,船上摇橹的“乌毛”不用化很大的力气,一枝小橹轻轻地一推一扳。只要船头领直把握好方向,不要和迎面而来的船碰撞就是了。只见他时不时的向对面的船呐喊“靠河来”,意即要对面的船从外面交会离我们的船远一点。对面的船也向我们的船呐喊“靠塘来”,要我们尽量往背纤的岸边靠。在岸上背纤的人比摇橹的人可着力多了,纤绳要拉紧了。一不小心纤绳还会被芦苇缠住,如果套不过去还得涉足从水中绕过去。最难的是“甩纤板”,这可是有一定技术含量的。沙地里的湾很少有那种有纤路的石桥,背纤的人可以从桥洞里走。沙地的桥是那种用几根毛竹或木头绑扎在一起的木桥和竹桥,背纤的人经过桥时,要走到竹桥上把纤板从这一头往那一头甩过去。右手高高地在空中度的一甩,左手则轻轻地一接,绝对是要一气呵成不能来第二回,除非是纤绳长还可以再来一次。背头纤的“大脚阿兴”看来还行,纤板都是甩过去的,否则是要拔了“桅头”,船才能从桥下过去。
出塘头闸,经六里桥、甘露庵,到讨饭张神殿横湾转弯向东,过祁门堂、八字桥,很快到了钱汉记。钱汉记过去是一个商号,凡商号都有一个装卸货的船埠头,船埠头就是小的船码头的意思。这里离我们要去的目的地,即“烂光明”已经不远了。我们知道‘烂光明“已经是后来的事了,这是后话。按钱汉记剃头哑巴的指点,我们的船驶入一条小湾。这条很窄的湾,叫党山湾,往南十余华里是萧绍交界的党山镇,往北不到2公里就是党山湾底。
(本文由网友魂系东沙连载)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