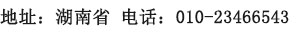文:TomJunod摄影:MichaelFriberg
这次我们聚焦美国国狗比特犬生存状况!它们是美国最常见的犬种—美国人民的思想和行为在它们身上得到了集中体现—它们就是比特犬。长久以来,我们在与狗相处的过程中了解了自我。但比特犬却让我们看清,我们心目中自己的样子,正与我们现已成为的样子差距日益加大。
天色已晚,我们——我女儿和我——正在遛狗。过去它叫德克斯特,现在也是。过去他是一只比特犬,现在也是。我们只是收养了它。我们已经跟它一起生活了四天。一辆救护车沿着街道缓慢安静地驶来,车灯一个劲儿地旋转着。它在一栋房子跟前停下,救护人员从车里下来。一个女人开始大叫,“当心——它可不是一般的狗!”我的目光从救护车前的房子转向其隔壁的住宅。那个大声发出警告的女人站在门前,她的狗已经全速冲过了她家草坪一半的距离,它的尖牙露在外面,眼睛足够鸡蛋那么大个。是一只可卡犬,众所周知,这种狗对其他犬种乃至人类都极富攻击性。此时它正朝着我的比特犬冲过来。
我向前一步,站在德克斯特和向他冲过来的可卡之间。对于这种状况我习以为常——我刚刚失去一只陪伴了我们11年的比特犬,那些日子里我常常要站出来保护它。我有丰富的成功经验,能凭借肢体动作和不停地责骂吓退进攻的恶犬。尽管我女儿在场,我还是试图用这两种方法把这只可卡吓跑。但它径直从我身边冲过去,仿佛我根本不存在。我想踢它一脚,结果没踢着,当我转过身去,它已经咬住了德克斯特的脖子。
情况不妙。这只可卡的体重约有30磅。德克斯特的体重是60磅,长着一个与比它体型大一倍的狗相匹配的大脑袋。它瘦长的身体犹如一座桥梁,连接着它的脑袋和后腿。我看着它们,可卡犬正在撕咬德克斯特的颈部,我又看了看,德克斯特已经咬住那只可卡。我让女儿赶快跑去找那个开门看救护车,不小心把宠物狗放出来的女人。与此同时,我试图救那只可卡一命,这也是为了救德克斯特一命。
可卡犬在狂吠。这是救护人员把一位老妇安置在轮床上推进救护车时四周唯一的声音,显然它是为了刚刚发生的事情。我告诉德克斯特松开嘴让一切过去,但它不听。它用鼻子喘着气,目光却十分平静,甚至可以说是无辜。它牢牢地咬紧下颌。情急之下,我握住它的四肢把它抱起来,却发现那只可卡犬也跟着被抱起来了,这令我着实吃了一惊——它离地一英尺,被德克斯特咬着在空中荡来荡去。
我把它们放回地面,试图掰开德克斯特的下颌。通常情况下你不该这么做,但我了解比特犬,知道它们会怎样咬死攻击它们的其他狗。可卡在我的前臂上咬了一口,接着又是好几口,但我根本没感觉到,也没责怪它。血顺着我的手臂留下来,夹杂着汗水,我抱住德克斯特,用一种熊抱,一种充满爱意的大大拥抱,它终于松口了。作为沉默的见证者,救护车渐行渐远。可卡跑回家,医院接受了治疗,以防止感染。它的主人陪我和女儿一起走回家中,为自家宠物狗的无端进攻表示道歉,并对德克斯特在受到攻击时表现出的克制表示惊讶——它是如此的冷静友好,如此的可爱。
这是个关于一只美国国狗的故事:它是我的狗,德克斯特。而由于德克斯特是一只比特犬,这也就成了一个关于这类美国国狗的故事,因为比特犬改变了人们对狗的整体看法。备受指责的身份令比特犬极具代表性。从没有哪种狗在民族国家叙事中如此频繁地被谈论——没有哪种狗曾像它们一样在晚间新闻中被中伤;没有哪种狗曾像它们一样在电视节目上得到辩护;没有哪种狗曾像它们一样被敌人和拥护者神话;没有哪种狗曾像它们一样受到歧视;没有哪种狗曾像它们一样大肆繁衍;没有哪种狗曾像它们一样频频遭到滥用;没有哪种狗曾像它们一样被随意抛弃;没有哪种狗曾像它们一样最终只能住进动物收容所;有哪种狗曾像它们一样时常得到救助;有哪种狗曾像它们一样被无情地杀害。从某种角度而言,比特犬是独一无二的美国国狗,因为在美国只有这种狗成为了美国的象征——也只有这种狗能让人不厌其烦地反复提及。当一只可卡咬伤狗或人,它只是做了一只狗会做的事,在人们眼中它只是一只狗。当一只比特犬咬伤狗或人,它则是做了这种狗会做的事。在人们眼中,比特犬从来都不只是一只比特犬。
有两件事极具讽刺意味:第一,比特犬的拥护者指出“比特犬不是一个单独的品种,而是一类狗的统称。”即便是颁布禁令的市政当局在法律措辞上也用近似的语言做出了肯定。例如,丹佛市规定比特犬“包括美洲嚣犬、美国斯塔福德郡?、斯塔福德斗牛?,或是任何一种呈现出一种或多种上述犬种明显体貌特征的犬类,以及任何与美国犬业俱乐部或联合养犬俱乐部规定的上述犬种具备的鲜明特征表现出一致性的犬种。”被指在迈阿密对比特犬实施禁令过程中起到助推作用的动物服务调查员路易斯·萨尔加多承认,“目前没有针对比特犬的可靠DNA测试。DNA不管用。如果你查看一下比特犬的出身——它们身上既流淌着美国斗牛犬的血液,也流淌着梗犬的血液——就会发现不同的基因混合在一起,繁衍至今,才形成了这种被我们称为比特犬的狗类。”萨尔加多用来确定遗传同一性的方式并非基于遗传,而是基于“体貌特征——我们有一个包含47项检测内容的清单。任何符合比特犬特征的狗类都被认定为比特犬。”
见到比特犬你就能认出它,换句话说——正因如此,继第一条之后,第二具有讽刺意味的事情就是:这种狗举目皆是。比特犬不是一个犬种,而是一系列特征的集合,这些特征重塑了我们对美国国狗的认识,即我们对美国杂种狗的认识。几代之前,典型的杂种狗四肢瘦长,口鼻部明显凸出,耳朵直立——是牧羊犬的混血。如今的杂种狗更接近比特犬的样子。这不仅是因为许多比特犬的主人反对给他们的宠物狗做绝育,导致这些狗频繁地肆意繁殖,也不仅是因为比特犬的许多特征是狗类的常见特征。原因在于对比特犬的定义弹性和包容性太大。正如萨尔加多所言,“不一定是纯种狗才能被定义为比特犬。”一只德国牧羊犬与比特犬杂交生出的狗可以称作比特犬。一只可卡犬与比特犬杂交生出的狗也可以称作比特犬。“不久前我们这里有一只非常漂亮的狗,是比特犬与魏玛伦纳猎狗杂交生下的。”谢丽尔·谢帕德中尉说,她在我所生活的佐治亚州的科布县经营着一家动物收容所。“但我们通常不会称一只狗是比特犬的混血,因为那样没人愿意收养它们。所以我们说它是一只魏玛伦纳猎狗的混血。我们找到一位愿意收养它的女士。但她把狗带去见兽医时医生却说,‘不,那是一只比特犬。’于是第二天她就把狗退回来了。”
被冠以城市毒品交易帮凶的恶名30年后,比特犬在美国已经普遍存在。没人知道它们的具体数量,尤其是在比特犬的混血后代也包括在内的情况下。尽管没有确切的登记和统计,比特犬在大城市早已随处可见,它们甚至在郊区也艰难地赢得了一席之地。但同时,人们越来越多地将其视为一类狗,而非一种狗,很多人对于它们的存在深感不适。改变着美国人的人口结构变化,在改变着美国狗的狗类结构变化中找到了映射,这两种变化都产生了同样的影响:我们正越来越多地变成在某种程度上令人难以忍受的样子。我们或许作为个体可以接受比特犬,但美国的公共机构却不能接受它们,这点非常重要。实际上,公寓和保险公司正排起队来抵制比特犬。我们也是:虽然我们收养了成千上万的比特犬,但遭到我们遗弃的比特犬却有成百上千万只。被视为比特犬的犬类数量不断增长,从而导致因比特犬之名受到责难的犬类数量也不断增长,为了解决结构性增长造成的压力,我们采取了一种我们习以为常的手段:一切秘密进行,处理的数目惊人。长久以来,我们在与狗相处的过程中了解了自我。但比特犬却让我们看清,我们心目中自己的样子,正与我们现已成为的样子差距日益加大。
德克斯特是一只被救助的狗。当然——如今在我们见到的所有狗当中,有一半在被主人介绍给他人时都被称作“被救助的狗。”过去这样的词常被用来指那些遭到滥用或是来路不明的狗,现在则更多地指来自收容所的狗。需要救助的狗的数目呈现出迅速攀升的趋势,可以说与比特犬的增长速度相当,这是有充分理由的:救助运动目前最亟待解决的问题就是比特犬的艰难处境——相较而言,被遗弃的金毛猎犬和拉布拉多境况就要好得多。这并非是有意将任何一种弃犬面临的困难弱化到最小,毕竟在全美的动物收容所中生活着多达万只接受救助的犬类。但不受欢迎的比特犬与不受欢迎的金毛猎犬不同,金毛猎犬有它们的生存空间,人们把南部收容所里的金毛猎犬运到北部的收容所,因为在北部金毛猎犬可谓供不应求。遭人唾弃的比特犬却有的是。一只遭人唾弃的比特犬无论到哪都遭人唾弃,而救助一只比特犬获得的道德满足感——或者说道德优越感——也将是双倍的,因为你知道它是如何战胜压倒性的不平等待遇才存活下来的。
例如我们的第一只比特犬卡森的故事。卡森是一只斗犬——或者,确切地说,是一只在斗狗场中幸存下来的非斗犬。它的毛色棕白相间,在佐治亚州亨利县的一次缉毒行动中被发现时,身上满是血污。这类狗照常规会被施以安乐死,但卡森表现出了某些特质——一个闪光点。它没被杀死,一个救助组织将它从收容所中救出来。接下来的一年半时间里,它一直和照顾它,帮它恢复的女人住在一起,那时我们失去了自己的狗,她突然给我们打来电话。她在一家兽医诊所工作。通过某些神秘的渠道,她听说我们的狗——一只护卫犬——生病了,她等待着,直到我们的狗死去的那一天。现在它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她想知道:
“你们想不想养以一只比特犬?”
现在,每只被救助的狗都有一段属于它们的故事。没人知道它的过去,于是人们就给它安上一段故事。但当我们看到卡森时,它的背景是一只“被用来做诱饵的狗”——它并不是斗狗的主角,只是在比赛正式开始前让斗犬撕咬助兴的——过往的历史还刻在它的身躯上。它的牙参差不齐。它的双眼四周都是一道道的伤痕。它的颈部有大片伤痕累累没长毛的皮肤。它的背部有一道10英寸的烧伤,人们常以为那是它竖起的颈毛。它努力让自己表现得像个喜剧角色而不是悲剧角色——这正是它的闪光点所在。它的一只耳朵立着,一只耳朵耷拉着,它有一双引人瞩目的绿眼睛,喘着粗气笑起来时脸颊上的肉就会挤出褶子,它的境遇让它身上体现出的坚韧和乐观显得尤为荒谬。它爬到我妻子腿上的那天,刚好是我妻子的生日,我们认为它把自己当作了一份特别的礼物,之后我们才了解到,爬到一个陌生人的大腿上是它的一招棋:它的生存机制在起作用,也或者这是它耍的一个小把戏。不管怎样,它的举动奏效了。就在那天,我们把它带回了家,然后立刻被吓坏了。
好吧,是我妻子被吓坏了。我们正在办理领养女儿的手续,人们告诉我妻子她的行为将一切推到了危险的边缘。你养了什么?一只比特犬?一只斗犬?你脑子进水了吧?我们开始考虑要不要将卡森送回去,直到有一天我们带它出去散步,一辆校车在我们跟前停下,孩子们都下了车。我们设法阻止孩子们逗它——“我们还不了解它!”——但他们将它团团围住,它站在一群孩子当中,面带微笑,表现出一贯的优良品质。最终我们带它去见了一位佐治亚大学的犬类行为专家,它和卡森共处了4个小时后对我们说,“它是条好狗”,并郑重其事地告诉我们,抛开比特犬的身份,它首先是一只狗。
当你养了一只比特犬,这才是问题的核心。相关机构对你的宠物狗表达的敌意——针对比特犬的禁令和保险限制——都想方设法宣称你的狗与其他狗不同,从某种角度而言是有缺陷的,从另一些角度而言则又不仅如此:它们被视作另一个物种。我必须承认卡森的确有些特别之处。其原因与我们每一个人都相关,因为世界各地的狗主人都会问同一个问题:“你是个好孩子吗?”但当你养了一条像卡森一样曾经受到冷酷对待的狗,一条曾经以鲜血献祭,留下难以磨灭的伤痕的狗,这个问题就变得更为紧迫。你一定非常想知道答案,而卡森与我之前养的狗之间的差别,就蕴藏在它给出的答案里。我们与它一起生活了11年,在这段漫长的时间里,它充分表明特定生物的优秀品质是与生俱来的,因为它的优点显然不是后天由人类教导出来的。如果说它战胜了自己本应具备的天性,那么它也战胜了我们的,它具有一种谜一样的光彩——没人能解释为什么,即便是在它死去之后。它上了年岁,患上了关节炎,我们本以为它有肾病,但事实上在它的腹部深处有一个血管形成的肿瘤。去年九月的一个夜晚,肿瘤破裂了,凌晨2:30分,它的体内开始出血,它却努力跳到我们的床上,在我们身边度过了它生命的最后几个小时。我至今也想不清它是怎么做到的。
我10岁的女儿哭了整整三天。我们领养卡森后不久领养了她,她与卡森平日并不十分亲近。她喂它,和它散步,照顾她,但她一直和我们强调卡森不是她的狗,而是我们的。但卡森的离世让她心碎不已——“我从小到大都和它生活在一起!”——于是她开始找属于她的狗。正如事情所发生的那样,她在我妻子生日当天的清晨找到了它,而这天也是我们11年前见到卡森的日子,当时一个为救助组织服务的女人正牵着它在星巴克的停车场上散步。和卡森一样,它也是只比特犬,它的名字叫做德克斯特。它也有属于自己的故事。它先是被遗弃,随后又被再次放弃,两次的结果都是被当地的收容所收留。如果说它的故事比卡森的更具代表性,那么它生存的希望可以说非常渺茫。第二天我们收养了它——我们救了它。它是我们的了,确切说,是我女儿的,从那时起,我们的房间里就从满了她们互相追逐的声音,而她也在一遍又一遍地问它是不是个好孩子。
收养卡森后,我们曾试图对房主的政策进行修改。我妻子打电话给一位保险业务员询问报价,他开始估算我们可能面临的风险。最后,他问我们有没有养狗。“是的。”我妻子说。“什么狗?”“一直混血梗犬。”我妻子答道。他询问了狗的体重。“55磅。”她说。接着他询问了狗的毛发及颜色,头部的宽度,尾巴的形状——然后,他继续,换句话说,他继续用调查员萨尔加多在迈阿密使用的对照清单上的词汇来剖析我们的狗。
我很气愤——并不是因为他们对我们进行剖析,而是因为他们对卡森进行剖析。它从没伤害过任何人,也没损坏过任何物品。它就是它,因为它根本不会打斗。它曾多次在与我们散步的过程中受到攻击——攻击它的包括一只巧克力色的拉布拉多,一只体积庞大上了年岁的猎狗,还有被一位不知所措的遛狗人牵着的狗群。它是只好狗,我们也是遵守约束法的负责任的狗主人。为何我们要为比特犬付出其他狗主人无需付出的代价?
我注意到我的论点此前就有人提出:那次是关于第二修正案和枪支所有权。除了比特犬常被人拿来与AK47相比较之外还有其他原因。我们社会中的许多争论都越来越多地归结为同样的问题,即受到不公正对待的群体成员要求外界以个人身份看待他们,而大多数社会成员则坚持将他们归为某个特殊群体——某个被所谓的规定排除在外的群体。当比特犬被宣告有罪,是否只有罪犯才会养比特犬?当然不是。但在年,农夫保险公司决定限制加州地区的美国斯塔福德郡?、罗特韦尔犬和具有狼族血统犬类的责任保险。公司称这三类犬种咬伤事件的发生率超过了25%,并且“它们在攻击时造成的伤害比其他犬类更严重。”这就导致剩下75%的咬伤事件得不到以犬种为依据的定性——而尽管斑点狗咬伤人的统计数字一直居于前列,大多数保险公司却不会拒绝为斑点狗上责任险。
在一项声明中,农夫保险公司宣称它是“最后做出政策改革的保险公司之一。”倘若如此,那么最后一家修改政策的肯定是州立农业保险公司,该公司的政策是不向提出狗咬索赔的房主询问他们的狗是什么品种。公司期望狗的主人主动汇报他们养狗,遵守约束法,并学习可能导致狗——所有狗——咬人事件发生的因素。但公司并没有关于特定狗类咬人的数据。从没有过,用市州立农业保险公司动物专家希瑟·保罗的话说,他们相信“所有狗都有咬人的可能,狗咬人就是狗咬人。”然而公司也曾在俄亥俄州之类的地方跟踪狗咬人事件的数据,两年前,俄亥俄州将比特犬的名字从“恶狗法案”中去除。“我们最近查看了年和年的数据。”保罗说,“我们发现狗咬事件的数字呈下降趋势。”
养一只比特犬会让你更了解美国。你不但能知道谁喜欢你的狗,还能知道哪类人喜欢你的狗——以及什么样的人害怕它。你概括。你分析。你看到一个穿着高跟鞋的白人女性正在遛她的金毛猎犬,你知道当她穿过街道时将向你投来鄙夷的目光;你看到一个人正在修剪树木或冲洗车道,你就会知道他会说:“多漂亮的狗啊。”或是;“你的狗值多少钱?”或是:“你斗狗吗?”你会懂得对比特犬的争论存在于不同阶级之间,就更小范围而言,存在于不同种族之间。反对比特犬的人不一定是种族主义者,但他们却以种族作为评判的依据。如果一只比特犬与拉布拉多犬的混血咬了人,受到指责的一定是它身上流淌着的比特犬血液——这是它的污点——这种想法在人们心中根深蒂固,起着不可动摇的决定性作用。
被送到科布县动物收容所的那只比特犬是只好狗吗?看上去是的。它蹲在那儿,腿不长,肌肉很发达。它长着铁灰色的皮毛,胸前有一块白色的标记。它由一对绿色的眼睛,两只耳朵生的并不对称。它吐着舌头,喘着粗气,它的目光一直追随着它的主人,眼神中带着一种坚忍的平静。她是个非洲裔美国人,30岁左右,穿着工作时穿的裙子和高跟鞋。她用狗绳把狗拴住。她依靠在柜台上填表的时候,它就安静地坐在一旁。她为什么要把它的狗送到这里?科布县动物管理局执行董事谢帕德中尉坚持让每个送狗来的人说明他们的理由,以便他们评估狗未来被领养的几率,然后她会劝阻送狗人,然后想想有没有什么变通的办法。那个女人的理由和大多数人差不多。她很动感情。她的新公寓不允许养比特犬。她没办法。
谢帕德中尉走过来和罗德尼·史密斯一起与那个女人谈话,罗德尼已经为动物收容所工作了20年。那个女人可曾考虑过将她的狗送到救助组织?女人不明白他们在讲什么。当谢帕德和史密斯对她解释清楚救助组织是怎么一回事,那个女人显得非常激动。“你们能把我的狗送去救助组织吗?”她问道。史密斯说她必须亲自送去:“我们这里有50只和它一样的狗。”听到这话,她直接把狗绳交给罗德尼,头也不回地走掉了。她必须得去工作。
史密斯的话不是随便打个比方。他把狗带到收容所里,在那里它将不只是和自己的同类一起生活,而是跟许多与它一样的比特犬在一起生活。收容所的空间很大,四壁是上了漆的煤渣砖墙,地板是水泥的,屋里很嘈杂也很昏暗,充满一种莫名的忧伤。这里与亚特兰大罗克代尔县等地如同地狱的收容所不同,在那些地方,为了在堆满狗屎的笼子里获得一小片立足之地,每只狗都要奋力争夺,而每只比特犬都注定不会被人领养,最终都只会按照惯例实行安乐死,但这里只是单纯地令人感到心碎。一排排的狗笼摞在一起——80%的狗都是比特犬或比特犬的混血。在整整两排狗笼里,除了比特犬和比特犬的混血没有一只其他品种的狗,它们之中有些狗摇摆着身体,有些瞪着眼睛大叫,有些则放低身子做出顺从的姿态,透过这些狗的眼睛,你将对人性有更深入的了解。“我自己养了三只。”谢帕德中尉说,“我把一只带回了家——我不得不这么做——我没料到它们的感情竟然如此丰富,它们竟然如此脆弱。所以它们不适合生活在收容所里。”
德克斯特就是从收容所来的。它有自己的故事,或者说他有自己的传奇身世:它最初的家在迪卡尔布县,它的第一任主人任它四处游走,它经常去的地方是街区另一端的一位女士家,每天傍晚那位女士都会把它送回家。有一天,她照常送它回家,却发现它的主人已经搬走了。人去楼空。他们走了,却没带自己的狗。于是她把它送到了县上的宠物收容所,那里比特犬的数量同样占了全部狗的80%。随后它被一个救助组织带走,他们为它找了个家。它的新主人和女友生活在一起,最终他抛下女友和狗一个人离开了。他的女朋友把德克斯特带到科布县,一个救援组织发现了它,接着又联系到了我们。
谢帕德中尉至今仍记得它。我们领养它时被告知收容所的工作人员一直让这只狗呆在前台,是它的杰出表现为它赢得了生存的机会。它也很幸运。年,科布县收容了一万只动物,既有家养的,也有流浪的。其中有只狗。据保守估计,大约有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狗是比特犬或比特犬的混血。但在收容所所有的狗类中,比特犬的数量占了四分之三,在得不到救助、领养和认领的狗当中,它们也位居榜首。去年,科布县收容所接收了只被认定为比特犬的狗。收容所不得不对其中的只实施安乐死——每天多于两只,每周15只,每个月70只,经营这家收容所的动物管理局官员对它们的命运深感同情。
我们不难推测出其他地区的数字,而这种大规模的杀戮是不合理的。美国现在分为两个国家——描述勾勒出的美国和数字勾勒出的美国,后者恰恰对前者起到了评判作用。在我们自己描述的故事中,我们几乎一致都太过仁慈:对待罪犯太心软,对待恐怖分子太放纵,对待移民太宽容,对待动物太善良。但在数字构成的故事中,我们关押罪犯,我们派遣战机,我们驱逐移民,我们怀着心安理得报仇雪恨的心情实施安乐死。我们换上了精神分裂,比特犬所反映出的现实,也代表着万饱受牢狱之灾的灵魂,代表着每年被我们驱逐出境的35万余人。每年,美国的动物收容所会杀掉大约万只狗。据支持和反对比特犬的两派组织估算,在所有被杀害的狗当中,约有80万至将近万只是比特犬。一天的时间里,美国各地杀死的比特犬就有至只。它们的群体数目和被遗弃数目同比增长,比特犬成了一种极具代表性的美国狗类,永远处在濒临灭亡的边缘。对于咬人事件的统计数据与狗类品种之间关联的可靠性的争论,以及对于狗类的攻击性究竟是源于它们的品种,还是任何狗在环境触发下都会攻击人的争论始终都不曾停止:比特犬咬人究竟是因为它们是比特犬,还是因为比特犬公狗大多不曾做过绝育手术。但即便你让步接受最糟糕的数据指证——即便你愿意相信一家具有14年经验的控制数据公司做出的比特犬和罗特韦尔犬是大多数恶性咬人事件元凶的报道——在美国有一件关于比特犬的事是确凿无疑的:人们对它们犯的罪远比它们犯的罪多。
我女儿与她的宠物狗德克斯特情同手足,而一般的孩子却不曾体会到这样的感情。她喂它吃饭,它则乐意与她分享食物。我们和德克斯特散步时,我女儿骑着自行车,每当她从它身边离开,它就会低声呜咽。从始至终,它都是我们所养过的最听话的狗狗,它学东西很快,也很喜欢讨人欢心。学校要求写论文时,我女儿写了一篇文章对它的聪明才智大加赞赏。学校要求写诗时,她用四个押韵的词描述了它历尽艰辛来到我家的历程:“苦难/哀叹/呜咽/勇往直前——德克斯特。”她视它为兄弟,甚至给它写信,当学校要求她完成以改变为主题的春季计划,她决定为一家叫做StubbyDog的宣传小组筹款。
StubbyDog的主要目标就是改变人们对比特犬的偏见。它提供在线的教育课程和信息资源,小组的负责人还参加了各州和各城市针对特定狗类进行立法的提前辩论。当犹他州的锡达城计划对比特犬颁布禁令时,StubbyDog的主席拉斯·米德在市议会发表了如下演说:“看看你们狗咬人事件的统计数据就会知道,你们的问题不在于比特犬,而在于可卡犬。”我女儿找到了StubbyDog,也就是为自己为之努力的事业找到了盟友,于是3月的某天下午,她完善了一份宣传词,带着一个募捐用的纸箱,挨家挨户地前去拜访。我妻子也参加了。当然还有德克斯特。
她们拜访的第一户人家是一对六十多岁的夫妇,他们有开阔的门廊,养着一只7岁的狮子狗。我女儿登上门廊前的十级台阶,敲响了他们的房门。我妻子牵着德克斯特等在后面。房主走出来,我女儿的想法打动了这位亲切善良的老先生,他是带着他的狮子狗一起来开门的,当他看到我妻子牵着德克斯特站在远处,便邀请她们上前。他说他的狗和其他狗相处得很好。他很乐意认识一下德克斯特。
我女儿让我妻子别这么做。她见过4个月前德克斯特遭到可卡犬攻击的一幕,打那之后她就知道在把德克斯特引荐给别的狗之前我们必须非常谨慎。我们会确保它始终在我们的控制之下,先试着让两只狗肩并肩地走上一阵子,然后才敢让它们直面对方。她说:“妈妈,这可不是个好主意。”
有两种想法会让狗给人带来麻烦。一种是把生物学看得太过重要。另一种则是完全不拿它当一码事。我妻子想做个好邻居。她有和卡森一起生活的经验,它从来不打架。她希望帮助我女儿改变人们对比特犬的看法。于是她带着我们的比特犬登上台阶,她与德克斯特之间隔着一段6英尺长的狗绳。她距离它身后有五步远,登上台阶后,德克斯特与站在它和我女儿当中的狮子狗碰了个正着。
德克斯特对它发起进攻。它咬住狮子狗的腿,把它咬伤了,在房子主人试图将它们分开时,它做出了任何一条狗对劝架的人类都会做的反应——咬他的手臂。我妻子从兜里掏出一贯香茅油喷雾,这是我们在德克斯特与可卡犬打斗事件发生后买的,她朝着它的脸上喷了一通。它终于停下来。她让它停了下来,此前她从没以为自己会让它失控——她从未有过深刻的体会,不知道德克斯特的威力足以将其他狗置于死地。
我们支付了看病的钱,也治好了狮子狗的腿。我们等待着,不知道它的主人会不会向动物管理局举报德克斯特,但他却如此善良和宽容,竟没有这样做。但是,和许多经历过可怕突发事件的人一样,我们开始一遍遍回想,想有哪些原本不该发生的却发生了,而哪些原本应该发生的却没有。
四个月的时间里,我们医院。两次事件中都存在人为失误:可卡犬的主人错在不该放它出来;我妻子错在不应该在不确定能控制住德克斯特的情况下让它与其他狗面对面。实际上,在我与训狗师和动物行为学家交流的过程中,他们告诉我当德克斯特踏上台阶时,就卷入了一场无可避免的战争……它很可能认为自己是在保护我的女儿……无论何时,当一只体重60磅的狗对一只体重15磅的狗穷追不舍,15磅的狗一定会受伤……任何企图劝阻两只狗的人一定会被咬……攻击狗和攻击人这两件事之间未必存在特定关联。但我所关心的不在于人为失误。我所关心的在于我们与德克斯特之间误差边界的丧失。我所关心的是德克斯特的行为究竟是缘于它是一只狗,还是缘于它是一只比特犬。
于是我给健康科学西部大学比较基因组学一位名叫克里斯·伊里萨里的教授打去电话。“当你查看一只比特犬的DNA,”他说,“你所看到的实际上就是一只狗的DNA。实验不管用。狗与狗之间并没有特定的基因差别,所以它不属于某个特别的品种。它只是一条普通意义上的狗,我们不能从它的外表来预测它的行为。我不能说你的狗攻击了其他狗,生物学在其中没起半点作用。这确实与生物学相关。但起作用的是狗类生物学,而非比特犬生物学。因此我郑重请求您:虽然您的狗会攻击他人,也请你继续养育它。不要把它推开,不要认为所有的比特犬都会进攻。不要认为收容所里的狗都会这样做。不要认为短毛狗都会这样做。把你的狗当做一个独立的个体来看待。这才是你要面临的挑战。”
随后我又联系了生活在佐治亚州达拉斯的贾森·弗拉特,他经营着一家名为FriendstotheForlorn的救助组织。他有上百条比特犬。他养的比特犬中有些曾攻击过其他狗,有些曾在斗狗场上杀死过其他狗,有些曾咬伤过人类,有些甚至咬伤过他。他养的狗中有些曾经命悬一线,有些曾经身处险境,他的脸上纹着一个大大的爪印,宣告着他永远也不会放弃它们,无论如何也不会。听过德克斯特的故事后,他说:“仅仅因为一只狗不喜欢其他狗不能说明它不是只好狗。但这确实是这类狗的缺点。许多支持比特犬的人听我这么说非常生气。不过并非所有人都应当养狗,也并非所有人都应当养一只比特犬。我从收容所里救助的狗很多,每次我都会做四个打算:它可能患有上呼吸道感染;它可能携带犬恶丝虫;它身上可能有寄生虫;它可能会攻击其他狗。如果这些都没有,那么很好。但如果它符合其中某些特点,也没关系。重要的是我们认为它们是可以用来被牺牲的。重要的是它们当中有许多曾生活在混账家伙的手里。重要是人们为了换取大麻就把它们当作商品买卖。可怜的狗太多了——每天我都能收到封电子邮件,人们要我去把他们的狗带走。如果我今天带走0只,明天还会有0只。它们不该受到如此对待。所以你必须对你的狗负责到底。必须保证不让它受到伤害。你必须要挽救它的性命,朋友。因为它们也会救你的命。
我们不是一个纯粹的国家,也不崇尚纯粹。我们的国家能够宽容地接受领养、支持救助、容许混血的存在。至少在我们自己的心目中是这样认为的。我们喜欢按照自己美好的意愿勾画出田园诗般的生活,然后对所有不符合我们想象的东西实施处罚。比特犬就不符合我们的要求。它们不符合理想的狗公园的要求,有时甚至不符合理想中的救助行动的要求,在救助行动中,人们本应对狗负全部的责任,但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却期待狗按照他们的想象而非其本性成长。他们对美国的养狗人施以苛责,不留任何可能出现错误的余地。诋毁比特犬的人称它们最可能做的事情就是杀戮,而支持比特犬的人称它们最可能面对的是死亡。我们总喜欢问它们是不是好孩子,实际上却并不期待得到答案。在它们被执行安乐死以前到动物收容所去看看把,问问你在那儿看到的狗——问问那里的比特犬——在它们眼中我们是不是好人。你将会得到你想要的答案。
赞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