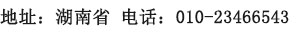口述:郑云再记录整理:孙和军
采访地点:马岙三江社区卫生服务站
采访时间:年6月13日
(一)
赤脚医生,是20世纪60~70年代“文化大革命”中期开始出现的名词,也是中国卫生史上的一个特殊阶段的特殊产物。
说它特殊,是因为当时新中国成立才十多年,“缺医少药”是一个很严重的社会问题。年,中国有多万卫生技术人员。高级医务人员90%在城市,只有10%在农村。医疗经费的使用农村只占25%,城市则占了75%。这是卫生部《关于农村医疗现状的报告》中提及的一组数字。毛泽东看到后非常不高兴,说:“广大农民得不到治疗,一无医生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这是毛泽东对解放以来医疗卫生工作做出的最严厉批评。
年6月26日,毛泽东发出了重要的“6·26”指示:“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全国卫生系统迅速掀起学习贯彻毛主席“6·26”指示的热潮,并大力发展和培训农村赤脚医生。
赤脚医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成为中国农村特有的医疗人员的称谓。
“赤脚医生向阳花,贫下中农人人夸。
一根银针治百病,一颗红心暖千家。
出诊愿翻千层岭,采药敢登万丈崖。”
乡村的赤脚医生通常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医学世家,二是高、初中毕业生中略懂医术病理者,三是一些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挑选出来后,到县一级的卫生学校接受短期培训,结业后即成为赤脚医生,可以治疗常见病,也能为产妇接生,主要任务是降低婴儿死亡率和根除传染疾病。赤脚医生没有纳入国家编制,也没有固定工资,许多人都是处于“半农半医”状态。他们随时要赤着脚,挽着裤腿、背着药箱,走在农村的田埂上,“随喊随到,有求必应”。同时也与其他农民一样,荷锄扶犁耕地种田。
(二)
我是年当赤脚医生的。
其实,从年起,马岙各生产大队普遍设置医疗保健员,主要负责给社员小伤包扎,打针服药,以防疫为主。重点防治霍乱、血丝虫病、脑膜炎、伤寒等流行性疾病。但是没多久人都散了。
当时我在马岙公社光一大队担任副大队长、第二生产队队长、大队团支部书记。队里缺医少药现象确实很严重。我们大队靠海边,张网人多,吃了不干净的鱼虾蟹,有时会吃坏肚子,常有呕吐、腹泻患者。那回大队里没有医生没有医疗站,医院也有一段距离,一有病人就得去请外地郎中来,很不方便,也耽误病情。上面有关部门看到了这个问题,我们大队里也下了大决心,决心培养一个乡村医生,来挑起这副担子。
年4月6日夜里,大队紧急召开了支部扩大会议,当场决定派我去参加医疗培训。由一个大队支部委员代理我第二生产队队长的职务,8日一大早,我遵照支部会议的要求,瞒着社员,独自去了干石览杨家部队营房。当时,定海县共有60多人一起参加这次学习培训,部队军医做我们的教官。学习时间不长,10天后,医院实习,一个多月后,便回光一大队,直接派用场了。
我一回来,就凑巧碰到了一个过路的外地人,在我们队里中暑晕倒。当时,大家都围着我,看我怎么救这个病人。大家都是一个村子里长大的,知根知底,对我这么出去一个多月回来就能治病救人,想想都有点不靠谱。我也是刚刚碰到一个实体病例,好像是老天故意安排给我的试金石似的。当时我根据培训期间所获得的针灸知识,仗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胆,在大家半信半疑的目光中,一枚银针下去。想不到立马见效,那外地人居然醒过来了。大家开始信服了,还真学会治病救人了,队里没培养错人。
(三)
年3月,马岙举办全社“赤脚医生”培训班,医院(原址盐仓虹桥,后迁至宁波)6个军医在中峰庙(今马岙中心小学)开门办学,我们大队三个生产队各抽上一人(未脱产),加上我,共四人,开始筹办大队合作医疗站。那年冬天到第二年的春天,马岙先后创办合作医疗站23所,培养“赤脚医生”82名,其中接生员23人,改变了农村缺医少药的状况。其中勤丰大队是第一家,我们光一大队是第二家。
年全面推行、普及合作医疗,西药也有了,各生产大队成立医管会,建立医疗站及医疗基金制度。集体为社员每人每月提取医疗基金0.15元-1.00元不等,社员看病按各生产大队经济收入不同来收取医疗费。有的大队收取医疗费30%,有的收取50%。我们光一大队是免费看病的,从年到年,一直如此。“赤脚医生”待遇实行的是工分制,一天计10分。我是大队里工分最高的。
年,黄疸性急性肝炎大流行,我们合作医疗站的几个赤脚医生用毛莨捣敷内关穴(位于前臂正中,腕横纹上2寸,将右手三个手指头并拢,把三个手指头中的无名指,放在左手腕横纹上,右手食指和左手手腕交叉点的中点,就是内关穴。可攥一下拳头,攥完拳头之后,在内关穴上,有两根筋,内关穴就在两根筋的中间位置)。毛莨对治疗胃痛,黄疸,疟疾,淋巴结结核,翼状铎肉、角膜云翳,灭蛆等有功效。再用茵陈草全民煎服,队里30多名患者,10几天后就治愈了,后来未再复发。
那时,我们都是上山自己采药,中草药和针灸等传统医药和医疗手段得到了广泛应用。
可以说,赤脚医生为解救中国一些农村地区缺医少药的燃眉之急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年,我记得是毛泽东主席逝世后不久,我和北海大队的顾耀阳,被派到舟山卫生学校复训班学习8个月,医院各科室实习了三个月。
(四)
我记得当时中国最有名的赤脚医生是上海的王桂珍。
年9月14日,《人民日报》转载了《红旗》杂志上一篇关于上海市川沙县江镇公社培养赤脚医生王桂珍的调查报告,介绍了王桂珍等人全心全意为农民服务的先进事迹。
当时,毛泽东主席看到这篇文章后,在文章的眉头上批示:“赤脚医生就是好”。这个批示经报刊公开发表之后,当年的中国大地上立即掀起了一股学习赤脚医生、学习王桂珍的热潮。王桂珍也被这种热潮渐渐推向了荣誉的巅峰。
年9月,王桂珍赴北京参加了赤脚医生中华人民共和国20岁生日庆典活动。年,王桂珍代表中国上百万赤脚医生参加了第二十七届世界卫生组织大会。这次会议之后,王桂珍的名气和影响越来越大。年拍摄的一部反映“赤脚医生”的电影《春苗》,即以她为原型。这部影片反映了20世纪六十年代我国农村缺医少药的情况,批判了医疗卫生事业走“高精尖”路线、为少数人服务的不良倾向,歌颂了农村赤脚医生的新生事物,响应了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号召。
这部电影当时很火,很多情节跟我们乡村的赤脚医生都很相似。所以,我们赤脚医生都以此为荣,也暗表决心,要扎根农村,为农民兄弟服务。当时,这部电影的插曲《春苗出土迎朝阳》,我们都会哼唱。
翠竹青青哟披霞光,
春苗出土哟迎朝阳。
顶着风雨长,挺拔更坚强,
社员心里扎下根,
阳光哺育春苗壮,
阳光哺育春苗壮。
身背红药箱,阶级情谊长,
千家万户留脚印,
药箱伴着泥土香,
药箱伴着泥土香。
翠竹青青哟披霞光,
赤脚医生哟心向红太阳,
心向红太阳。
(五)
我当时背着的那个红药箱,还是木头做的,背坏了好几个,后来换作皮做的了。那几年,《春苗》的精神激励着我们义无反顾地走门串户,主动到农户家里探病情。每年农忙时节,医院的医生都会下来,和我们这些赤脚医生一起,背着医药箱,巡逻在各片田头,给农民们送去十滴水等药品,有病况的就地医治,没医患情况的,我们也会下到田里,一起干农活。
血丝虫病是一种通过蚊子传播的寄生虫病,在当时十分常见,最典型的后遗症就是下肢严重肿胀,俗称“大脚疯”。民间曾经流传着“八人围桌坐,狗子钻不过”的民谣,意思是指腿肿得厉害,围坐一起中间没有缝隙,这是丝虫病危害的真实写照。
为防治血丝虫病和疟疾,每年到了10月,每个生产队的赤脚医生,每晚8点以后都会上门,给每个农民采血,就是俗称的“割耳朵”,即用玻璃在耳朵边割划点血出来,作为血样,在万倍显微镜下观察有无血丝虫病菌。一开始,有些农户还不理解,认为夜里敲门,让他们睡不好觉;有的自以为身体好,不用采血;也有害怕被白白割血,总之,不肯开门的人家很多,所以,为了尽量地少给农户增添恐怖和心理压力,我们都会在大队广播里提早两天进行广播和宣传。一旦发现有血丝虫病和疟疾感染者,当时就采用奎宁、佰氨奎宁两药合用,这药副作用也很厉害,反应很强烈,有人服用后曾出现了话多、神经质等现象,所以农户都不敢轻易服用,更害怕被诊断出得了血丝虫病和疟疾。
年,舟山卫校来马岙开门办学,成立了舟山卫校定海马岙分校,这也就是定海县卫生学校的前身。地址在唐家村敬老院,当时培养了光一大队的郑云女(女)、光三大队的林益祥、勤丰大队的林苏绒(女)、安家大队的安旭烈、王家弄大队的周秋燕(女)、五一大队的练岳钦共6个乡村医生。
(六)
碰到重症病号或需要动手术,合作医疗站无力治疗,我首先做的就是联医院,一医院。到了我手里的病号,在我没有医院前,我就是病人唯一的依靠,须臾不能离开的,这是我的从医原则。
大概50年之前的一个晚上,我们大队农民李利生急性阑尾炎发作,当夜风很大,漆黑一片。那回他们家里没钱,我家刚好卖掉一只大猪,有了54元收入。我说看病要紧,医院吧。这家人四个儿子,一个女婿,加上我,6人轮流抬着李,翻山越岭,摸黑走了2个多小时,医院,动了手术,住院10天,花了35元。医院治疗,那也是我们乡村赤脚医生的职责。李利生还有一次误服铅丝,铅丝横撑在其大肛前,痛不欲生,也是我帮他拿了出来。还有一次在外面干活,李利生中暑,也是我救了他。
年,我们大队里的老支部书记胡某,帮人家打石头,左腿不幸被巨石压断,我采取紧急止血措施,跟着救护车,隔半小时松止血带一次,医院。这种相对专业性的急救措施,医院的及时救治提供了最大程度的护理保障。
年,北海同兴大队徐罗庆才2岁的小孩,医院诊断为“中毒性菌痢”后期,医生劝徐罗庆放弃治疗算了。徐罗庆不忍心放弃,抱来给我,我和驻华旗山部队卫生院一个姓张的医生一起,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采用针灸治疗,在小孩四缝穴处挑血,再用抗生素针打下去,结果一个星期以后,小孩病愈了。这家人和小孩每年都会来我家拜年。小孩长大结婚时,请我去定海城北联谊宾馆赴喜宴,按照舟山风俗,舅公那一桌为最大,放在最重要位置,细心的新郎在舅公这一桌位子上都写着舅公们的序号名讳,以方便舅公们对号入座。我的位子也放在舅公行列,位子上却写着“救命恩人”。这新郎对我感恩戴德,在这一细节上都这么用心,着实让我感怀。为人医者,治病救人为天赋职责,我蒙队里和村员信任,培养我去当赤脚医生,为村民服务理所应当,这也算是我对村民的一滴回报吧。
(七)
年,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合作医疗解体,“赤脚医生”经甄别考试改称乡村医生,医疗站由乡村医生承包,改称乡村保健站或卫生站,自负盈亏,社员自费看病。
年1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不再使用“赤脚医生”名称,巩固发展乡村医生队伍》一文,到此“赤脚医生”逐渐消失。
但是赤脚医生的功绩不应当被埋没。相关资料统计,在上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中国人的平均寿命提高了很多,远远超出了同类发展程度国家。同时,疟疾、血吸虫等传染病得到了有效控制,而脑流、白喉、天花等流行病几乎被消灭。
中国以赤脚医生和合作医疗为主体的农村医疗保障体系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赞许。在年的一份考察报告中,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银行赞誉中国“以最少的投入获得了最大的健康收益”,并将这一模式称为“中国模式”,认为这一模式“是发展中国家群体解决卫生保障的唯一范例”。
一直到年之后,随着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在全国的再度兴起,人们又想起了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赤脚医生。
今年,我七十三岁了,还和我的两位差不多年纪的同事一起,承载着村民的信任和领导的信任,一直坚守在社区医疗服务站发挥余热。这就是我作为一个乡村赤脚医生的朴素情怀吧。
(多数图片来自网络)
孙和军海洋历史文化工作室
(欢迎转发转载敬请注明出处)孙和军。网名海山坐忘。舟山自由岛民。已出版海洋历史文化散文集《走读千岛》系列五部。人物传记《复滃风云》。诗集《蓝色图腾》。随笔《坐忘斋笔记》。与人合作编著《西方人眼中的近代舟山》《海上门户舟山》《东极之光》等。编著《画说新城》《金塘印迹》《流韵白泉》等舟山各地人文历史类书籍30本。
感谢您的阅读
赞赏
人赞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