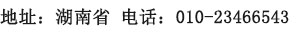戳上方“天涯社区”看更多好帖!
家国往事第30期:姥姥的文档
撰文
柏耀华
主播谢谢
先祖的传说我出生的山东临沂柏庄,一个半山半岭的小村里。祖辈以种田为生,有时为了支撑门户,家族也专供一个人读书,为族人求取功名,我三爷爷就是这样最幸运的一个。柏姓是比较少见的姓氏,我们那地方方圆几十里,也只有我们柏家庄一村较多人姓柏,其他庄上几乎没有,即使有,也是最近几十年,从柏庄迁出的人家。记得小时候,常听爷爷奶奶讲祖先的事:“我们老柏家是从山西喜鹊窝迁来的。来时一家兄弟四人,其中一个在柏庄,过去村名也不叫柏庄,叫东溪沂,后来柏姓人口占了大多数,不知什么时候就叫柏家庄了。其余兄弟三个一个去了石砬子,一个去了野里,最小的一个出家当了和尚。”关于老四和尚,还有一些美丽的传说,其中一段是这样的:老四和尚为了重修庙宇,外出化缘。到了南方,有一个有钱有势的大户人家,和尚向他索钱,不给,四和尚不走。其时正值隆冬,天气严寒,那财主家门前有一个石槽,槽内打满清水,财主说:你能在石槽里睡一夜,明天就给你钱。和尚说:一言为定。财主答应了。严寒的冬天,财主以为和尚一定冻死在石槽里了,谁知第二天早上起来一看,石槽里热气腾腾,和尚还活得好好的呢,他不得不按照约定的数目给了和尚钱。就这样,历经千辛万苦,四和尚化到了很多钱,回来重修了庙宇,亭台楼阁,休整一新,最后四和尚还留了一点钱。他有个私心,想把这些钱留给他的干女儿。有这份私心不要紧,他就长了一个搭背疮,怎么治也治不好,差点要了命。他知道,这是菩萨在惩罚他,私心要不得。于是,就把留下的钱修了一个东角门,疮才好了。若干年后,和尚坐化,临死,天将明,他让徒弟出外看看东方是什么颜色,徒弟回来说是红色。老和尚听了,知道自己终究未成正果。徒弟问师傅:我们什么时候再见面?师傅答:钟鼓齐鸣之时。于是圆寂。又过了不知多少年,小和尚已经成了大和尚。这一天,南方以为道台到临沂寺庙祭拜,庙里钟鼓齐鸣,每个和尚都忙着念经,做各种仪式,忙得不亦乐乎,礼毕,道台一行人马浩浩荡荡地走了,和尚忽然记起,老师跟我说过:钟鼓齐鸣时再见,我怎么给忘了。于是出去追,怎么能追的上?家史:请主我从记事起,家里就供奉着先人的牌位,临沂话叫请主。怎么回事呢?我们那时很多家庭都要请主。我们所请的“主”,既不是“天主”,也不是“菩提老祖”,也不是耶稣,是自己的先人、祖宗。具体就是把先人的牌位用石膏做好,放到主楼里,主楼,奢华点的可以精工雕出亭台楼阁,简单点的也有做个前面没有盖的长方盒子,站着,外面加个没有底的盒子套上。把先人的牌位成双成对的排列在里面。夫人多的,后续夫人单放。另外还有一幅大的家谱,有用纸做的,有用布做的,可以悬挂。各家的家谱,都是由家族里最有权威的像族长一样的人家来请,平时就放在这家人家里。放在哪儿呢?一般都是在这家的最尊贵的地方,我们那方言叫上岗,就是堂庵正门所对的北墙。我家的情况是:在北墙上方,离房檐大约四十公分的地方,楔了两根木橛,上樘一块长约一米,宽约二十公分的木板。家谱、主楼都放在上面,只有到年三十那天才摆出来,一般到大年初二或者初三送走。送走的时候,由本族的长辈带领男丁,到林里或者大路上烧点纸,也就是让祖宗们回家享用后,再发点钱,就算送回去了。回家把供桌收了,好吃的糕点、水果给孩子们分着吃了,家谱、主楼重新收好,全部仪式就算完成了。我们家的家谱可能是我老爷爷那时候开始的吧。因为老爷爷兄弟四个,我们家族里也只有四家每年都请主,一般人家没有请的。我们家的也被称作老四支,因为我老爷爷是四兄弟中最小的。各支请的都是各支的先人及更早的祖先。每逢过年,按支分开,各支人丁先给自己的老爷爷磕头,然后在互相磕头,之后再去更远的族人家磕头。我们家族兴旺,人丁兴盛,每逢过年,磕头的大军浩浩荡荡。天色微明,吃早饭前,是男人的祭拜时间,饭后,是姑娘、媳妇磕头的时间。十点后,才是老太太们给祖先磕头的时间。因为上午的前面大半时间,她们都得在家等着接受晚辈的祝福、磕头。磕头时,都是晚辈给长辈磕,所以辈分越大,该去磕头的人家就越少,这样老人们一般只到请主的人家去磕就行了。我记事到十几岁时,早上发完纸,吃完饺子,就跟同辈的姐妹几乎逢门便磕,一路对老人说着各种新年祝福的话,真是有趣。除了同姓人家互相祝福外,有时也去外姓人家磕头,像后街上老申家,庄西前街上老卢家,他们家族里也有许多到我们家来磕头,互相祝福、问候。请主的仪式大致是这样的: 每年除夕,杀鸡、买鱼,做贡菜,还有各种能弄到的干果、水果,象山楂、柿饼、糖果之类,还有我娘亲手蒸的各色花馍馍。有一年,有一个我奶奶的亲戚从东北回老家过年,路过临沂城,从城里捎来桔子、香蕉,送给我家不知几个。我只记得供桌上有一只桔子,一根香蕉。我们姐弟几个都想尝尝,但谁都不敢去动,只能眼巴巴地瞅着。年初一,我大爷领着他的二小子来拜年,拿桌上的水果给他儿子吃,拿桔子,不要,于是拿了香蕉,高高兴兴地走了。我比他的这个儿子大两岁,整天在家,看在真真的。因为这根香蕉,心疼了好多天。想到香蕉发出的阵阵香气,就琢磨一定非常好吃,但终究不知是什么滋味。越想越觉得心疼,于是这件小事,就永远留在了我的记忆中。家谱是一张三尺宽,六尺长的壁画做成的轴子,上面是一副松鹤图,我的先人就隐映在苍松翠柏之间了。另外就是主楼了。据我奶奶说,主楼是我做官的三爷爷回家安葬我老奶奶时出钱修的,一共三座,是木雕楼房,每座楼底座长约四十公分,宽约十五公分,高约四十公分。硬木雕成,楼顶老式小瓦,像倒起鱼鳞排列得错落有致,煞是整齐。楼前回廊,内供秀才亲自撰写的牌位两尊,分别是我老爷爷和老奶奶的,牌位是用白底石膏做成的。另外两座是我爷爷的爷爷和奶奶。我爷爷有两个奶奶,头一个奶奶年纪不大,生下四个儿子后得病死了,后续娶二房奶奶。二房再没生育,只把前房的孩子抚养成人,所以功劳也很大。后人也为她同样筑楼,单独供奉。每年的除夕,大人们忙着剁馅子、炸年货、做贡品,我们小孩就到处跟着看热闹。只等午后,傍晚时分,我爷爷带领众位子孙,把老祖宗从堂庵正中后墙的阁板上请下来。先挂上壁画家谱,从主楼里请出牌位摆好,上好贡品,摆好筷子,斟上酒,供桌的两边摆上长凳,然后就拿着烧纸到大街上烧了,磕头,磕完头,回家再烧上香,烧了纸,就算把祖宗请回家过年了。众人散去,各回各家,小孩子到街上去玩,大人们在家坐着守岁,有时去烧点纸,告诉先人们:拿钱去花,也多多保佑家中老少平安、发财。除夕的夜里,供桌上的东西是不能动的,两边的凳子也是不能坐的,因为那都是供先人们享用的。可惜这点家史文化,在年那场文化浩劫中,被当做四旧收去砸掉、焚毁了。从此再也没有那么精致的主楼与画中家谱了。族人我的族人是很兴旺的。听我爷爷说,他的爷爷弟兄两个,他爷爷是老二。老二有四个儿子,女儿就不知有几个了。两个老婆,前面已经说过,第一位早逝,第二位没有生育,把前面的孩子抚育成人。老四叫柏玉全,也就是我的老爷爷。因为他最小,最需要母爱,他也最听话,最乖,所以得到的关心最多,虽然是后娘。我的老奶奶也很善生养,一口气生了六个儿子,一个女儿,我的爷爷最小,从小我就听人们称他柏老六。我大爷爷柏洪印在家,人身体好,头脑也灵活好使,所以在村里也得上是个人物,无论村里有什么事,都是领头人物,可惜那时穷,医疗条件差,刚刚二十七岁,就得肺病死了,留下两个儿子。二爷爷和三爷爷、四爷爷都是东北,有的在黑龙江,有的在吉林。 说起二爷爷和三爷爷,还有一段故事。家中那么多儿子,就想供一个上学,因为老大得帮着家里干活,就叫老二去上学,安排老三放牛。老二不想上学,就跟老三商量:你去替我上学,我替你放牛。老三小,正愁着去放牛,就答应了。老二牛放得好,活也能干,老三可能天生就是读书的料,上学一直名列前茅,从小学、中学,一路读到大学,到南京读了法政大学,以后被派到黑龙江安宁县做县长,老二就在家务农,这就是小孩子不懂事,一个玩笑的举动,却命运天差地别。 五爷爷也在老家,刚娶了媳妇,一个孩子还没出生,因为穿了得肺病去世的大哥的一个小皮袄,也得了肺结核送了命。当时,大哥有一个很漂亮的小皮袄,送到了当铺里,老五很喜欢这个小皮袄,就赎出来穿了,结果也传染上了肺结核。据我奶奶说,他死后一段时间,他的儿子才出生。当时因为孩子头大,难产,好几天生下来。孤儿寡母过日子非常艰难。孩子生病,没钱治,后来孩子死了,五奶奶就改嫁了。从此,五爷爷一家就消失了。我的爷爷名叫柏洪喜。他小时候的事,他不说,我也无从知晓。只听说我奶奶也是个苦命的孩子,虽然也是大户人家的女儿,但非常不幸,从小死了父亲,母亲被迫改嫁,她只好跟着一个后奶奶在众位叔叔、姑姑中长大。她的亲奶奶非常能干,太能干了,没黑没白地干活,完全不顾及自己的身体,只有二十多岁就生病撒手人寰,留下三个儿子。男人死了老婆,续娶二房,这回知道心疼老婆了,不让她干重活,所以又生下四男四女。加上前房的儿子,共有七个儿子,组成了一个非常庞大的家庭。我的老姥爷排行第二,在生下我奶奶不久,得了伤寒病,昏迷不醒,他后娘给他发汗,装了一罐开水,放在他床上,他没注意,把水罐弄倒,烫死了。这样,我奶奶爹死娘改嫁,成了孤儿,在奶奶的家里,靠着叔叔、婶婶、姑姑的关心慢慢长大。后来,可能是在我老姥娘,她的改嫁了的亲娘的撮合下,嫁给了我爷爷。(我老姥娘改嫁的村子离我们柏庄不过二里之遥,叫做候家窝,她改嫁后再没生养。)我小时候我老姥娘经常来我家,奶奶也带我去过她家,所以我想可能是她有意将唯一的女儿安排在自己身边。小时候我只知道奶奶的娘家在候家窝,怎么又说是东安静呢?长大了才明白其中曲折。候家窝现在改名建设村,在柏庄的东北方向,背靠茶叶山,村子建在山脚下的岭地上,出门就是石头,却没有整装石料,村里的人大都很穷。 我奶奶身材高大,年老后还足有1.65米。老姥娘却很矮小,红脸膛,长方脸,两腿很粗,可能是因为得过血丝虫病留下的后遗症,两条小腿都有对掐还粗。我还没上学,大约五、六岁的时候,奶奶领我去老姥娘家,一路走着沟沟坎坎,到处都是石块的羊肠小路。记得老姥娘到我家时常说,她每次来我家,都把道上的石头捡干净,怎么下次来的时候又有很多石头呢?她很生气。我跟着奶奶一路玩,一路走,就到了一个到处都是用小石块砌成的村落。老姥娘家没有大门,甚至没有完整的院墙,只有半截院墙,另一半留着曾是院墙的旧迹。两间草房又低又矮,不分里外间,所以屋里的所有一目了然。东墙靠南放着一张不知经过多少代的小木桌,黑色的,上面放着简单的铺盖。门的东面用三块石头支起一个最小号带耳的小锅。我们去时,她刚做了一锅秋梅豆的渣豆腐,里面有很多整个的大梅豆种,非常好吃,我吃了很多,至今不忘。其余吃的什么就不记得了。老姥娘是一个孤老太太。因为我奶奶是二月初二的生日,那时候还天寒地冻的,老姥娘那时年轻,不知避寒,月子里在雪地里大小便,坐下了病,所以再也没有生育,到老成了孤老太婆。能走动时,偶尔到我家去住住。最后的岁月里,走不动了,也就不去了。最后在年,生活最困难的时候,寂寞地死去了。当时我爷爷在56年迁民去了黑龙江,随我大爷走了,没在家,奶奶也正病得下不了床。所以老姥娘的后事就由我娘代劳了。什么梳头、洗脚、穿老衣,最后还由我娘抱着头,她本家的一个侄媳妇抬着脚,弄到了灵床上。这是我娘亲口对我说的。以后出殡、提壶泼汤,一一代劳。我奶奶当时得的也是肺结核,每天午后发烧,咳嗽。因为当时父亲已经调到乡党委工作,以后又在管理区任书记,所以很少来家,但是由他请的医生时常来给我奶奶看病、开药。那时已经有了治疗结核病的特效药,再加上有我娘的精心照料,还有后来我大爷又领着我爷爷回来了,一家人又得以团聚。所以我奶奶的病,虽然历经两年,最终还是好了。享年九十七岁,做到了五代同堂,玄孙已经五、六岁,子孙上百人。这在村中是很罕见的。我奶奶常跟我说:我老爷爷在的时候,也是一个很清秀的老头,白胡子,手里拿着长烟袋,穿戴的也还整齐。一次,一个牵骆驼的人从我们村里路过,遇到我老爷爷,看了看他的面相,说:你老人家有福,能有十六个孙子。说得我老爷爷很高兴。当时的孙子可能还不够这个数,过了一段时间,我父亲等人陆续出生,正好十六。所以我奶奶一直夸牵骆驼的相面准。老爷爷具体享年七十几岁,无从考证,我爷爷属马,是七十六岁上,农历年腊月二十几,阳历可能是71年一月份去世的。我们家跟东北有很深的渊源。奶奶说过,过去因为生活所迫,爷爷也去过几次东北。因为我们老家很多人都在东北,来去自然方便。其中一次是我爷爷自己去的,可能长时间没给家里捎信,把我奶奶急得吃不下、睡不着的。当时邮政所很少,最近的一个设在离我家二十五里地的半程。为了看有没有她的信,我奶奶一大清早,就颠着四寸的小脚,亲自跑到半程,走到时,人们才吃早饭。信淘到没有她没说,只听她说那里的熟人都赞她走得快,去得早。在三年困难时期,由于吃了食堂,菜园也不让种了,根本没有菜吃,既缺粮,又缺菜。只有采点树叶当菜吃。树叶里面,榆树叶子、国槐叶子算美味的,很难采到。有时弄到点,就是一大家人的享受了。我们吃过柳树叶。采来叶子,下锅煮了,清水淘了,加上点盐,就卷煎饼吃了,虽然又苦又涩,但当时饿极了,也觉得很好吃。各种野菜就是我们的主菜,什么灰灰菜、野银子菜,都是最好的菜,很难找到,最无菜可挖的时候,我爷爷连路边的苘麻都拔来吃了。这时候,我奶奶就回忆起东北的好来。说她年轻时带着孩子在东北逃荒,出门到处都是大车轱辘菜(也就是我们这叫车前草的),水荠菜,“不缺菜”,口中说着,眼中流露出的那种又满足、又渴望的神情,我看着也跟着羡慕半天。又说,她一次出门到沟里洗菜,看到很多大石块在水里,在上面蹲着洗菜真是太好了。于是她就找了一块靠水近的蹲上去洗起来,洗着洗着,石块怎么动起来了?仔细一看,哪里是石块,分明是一些鏊子那么大小的老鳖趴在水里。吓得她拿起菜,一溜烟地跑回了家。可见过去人少地广,各种生态保持得多好!她们闯关东可能就奔我三爷爷去的。那时,三爷爷在宁安做县长,我爷爷很可能给他打杂。鞍前马后的跟着,不知深浅,总认为是自己的亲哥哥,所以跟的很近。这使我三爷爷在外人面前很尴尬。因为他官帽衣着整齐,我爷爷一身破衣烂衫短打扮,走在一起,太不协调了。可能忍无可忍了,一次他直接跟我爷爷说,“六份里,以后在外人面前不要跟我走得太近了。”以后,再出门,我爷爷就远远地跟着,不敢靠前半步。虽然爷爷是投奔他哥哥去的,但一个家庭住城里大宅子,一个家庭住山沟钻茅草棚屋,因为穷人只有在山沟里才能刨出吃喝。我奶奶就领着孩子在山沟里半粮半菜,也替人缝缝补补地生活。爷爷给三爷爷打杂也只能混个肚子饱,补贴不了家里什么。我奶奶给家人做双鞋的布都没有。一次,我奶奶给混关东的穷兄弟加工了件衣服,剩下点布弯,才给孩子做了两双鞋,别人看见还羡慕得了不得,可以想见做件新衣服有多难。有个熟人看我爷爷家里人衣裳破烂得不堪,看不过去,就跟我三奶奶说:“你翻翻箱子底,找点布,叫六份里回去给孩子做个衣裳穿。”这也没能说动,没听说我奶奶收到什么布。那时候,我二、三、四爷爷,加上我爷爷,至少兄弟四家都在那儿。我老爷爷可能已经过世了,就把我老奶奶接去住着。我老奶奶很有做婆婆的威严,平时单独吃饭,病了,媳妇轮流服侍。她很会折腾人。最严重的是:她下炕拉屎都撒在地上。她住的房子是方砖铺地,屎尿就都灌到砖缝里,打扫起来很费劲。有人问她干嘛不拉到便盆里,她有她的理由,说她的儿媳妇们,“叫些小×们闲着干什么?就得找点事儿给她干。”她就这样在儿媳妇们面前逞着威风,对供她吃住的三儿子却也没什么办法。每年她的生日,我三爷爷都要张灯结彩,大摆筵席。把老太太打扮起来,坐到太师椅上,红毡铺地,众位达官贵人,亲朋好友,都骑马坐轿,抬着礼盒来拜寿。老太太像木偶一样,被摆弄了一整天,眼看着成堆的钱财物品,大饱眼福,可也只能饱个眼福,过一夜,就都不见了。不知这样过了几个生日,老奶奶坚决不当傀儡了,要回山东老家。这样我爷爷奶奶就又回山东老家伺候着她。关于我老奶奶,我听到的轶事还有一些。她总共生了六个儿子,一个女儿,闺女最小,就是我的姑奶奶。这个小姑奶奶嫁到了南边邵双湖一个姓郑的人家,姑爷爷叫郑凤祥。此人身材魁梧,高鼻梁,大眼睛,两撇扫帚眉,据说他先天声带撕裂,说话瓮声瓮气地不太好懂。他好喝酒,不醉不散。我姑奶奶跟他生了两个儿子,五个女儿,五十多岁因为神经病死了。我姑奶奶年轻时走娘家,在我奶奶家过夏天,跟着我奶奶吃小锅饭,一起到街上在树下乘凉:纳鞋底,做针线。夏天,水多,鱼多,有来卖小鲜鱼的,姑奶奶就称了一斤。我奶奶就没这个权力,因为她没有钱(钱我老奶奶管着),也不能随便买东西。拿回家,我奶奶高兴得了不得,因为她也爱吃鱼,可以沾光跟着吃点儿。俩人正在择着,我老奶奶说话了:“能吃海鲜,不吃湖鲜。大热天里,这小烂鱼能吃吗?”她们姑嫂俩谁都不说话,心里清楚:海鲜,湖鲜只有你自己吃,别人谁能尝着?况且,她俩都年轻,又正奶着孩子,急需营养,能吃上点小烂鱼炒辣椒就很满足了。我老奶奶给自己花钱很大方,因为她在家里掌握着一家的财权,平时花钱由她三儿供给,不够用了,秋天打下粮食,就挎着大箢子去卖粮食,闹得子孙们春天挨饿。那时我们庄上有集市,买、卖都很方便,出门就到。老奶奶活到大约八十岁吧,因为她净吃好东西,最后可能是死于便秘。 我问奶奶,老奶奶是得什么病死的。奶奶说,也没什么病,就是拉不下屎。冬天冷,她本身就不爱动,天天躺在床上,吃着各种好东西,什么点心、鸡蛋、猪肉、咸鱼、果品。(她吃最好的,儿子和孙子们吃次等的,媳妇只有吃糠咽菜的份儿。)时常说要大便,我奶奶就把一个大葫芦瓢到火上烤,里外烤热,给她拿到被窝里,半天拿出来,瓢里还是空的。越这样,越吃不下东西。我问,她总得吃点儿什么不。奶奶说,就是吃个鸡蛋,栗子什么的。也请过医生,医生也看不好。所以我估计就是便秘,又不好意思跟医生说拉不出屎,光说有病,医生也诊不出来什么病,也不敢给她乱投药,时间长了,上下不通,就死了。我奶奶可能从我老奶奶身上总结出了经验,老了以后,感觉有不通,就自己调理。夏天多吃瓜菜,冬天多用萝卜汤。虽然那时候没什么好营养,也活到了接近百岁。 我爷爷闯关东时,不知给谁养过马、牛、骡子这类大牲畜,期间接触到了很高明的兽医,学会了给牲口看病。他没上过一天学,一字不识,但凭着惊人的记忆力,学会了给牲畜扎针,开药。经他看过的牛马,几乎无不痊愈。在我们那里,方圆几十里,谁家的牛病了,只要还能走,就牵到我家门口治疗,不能走的就把我爷爷请去看。我见过我爷爷给牲畜看病,大体是这样的:先看看牛的样子,精神状态,再用手摸摸牛的前肩部位、牛鼻子,问问吃草的情况,就判断出得了什么病,该用什么药。就找一个会写字的,爷爷说着,什么什么药,分别多少,开好方子,就找人抓药去了。然后,我爷爷一边跟人说着话,一边就开始给牛下针。先找棵大树,把牛栓好,缰绳尽量栓短,短到牛头不能随意摆动。给牛扎针可不是容易事,一是牛不让扎,二是牛皮又厚又硬扎不下去,这也算个技术活,看爷爷给牛扎针,就像看人耍杂技,非常有趣。每次有人牵牛来看病,我都跟着看。爷爷栓好牛,就喊:远着远着,都站远点儿,别让牛碰着。我们就退后好几米远,站着看。这时候,爷爷就从腰里掏出针包,开始下针。针包是皮的,像个黑色的大钱夹。里面排满了各种针。我记得有一根叫劈针,针柄不算粗,针头是扁的,接近一厘米宽,像老太太的修脚刀。还有几根大大小小圆杆尖头的三棱针,几根圆杆,偏头像标枪形状的。根据不同的疾病,用不同的针,在不同的部位下针。有的牛只刺鼻子,有的针膝盖。我那时候小,不懂牛的病,不问,爷爷也不说。只记得很多牛都得刺鼻子,一针下去,鲜血滴滴答答地开始流,先是滴到地上,后来血一流出来,牛一伸舌头,就舔吃了,血不流了,牛也好了。如果是在膝盖下针,就见牛膝盖附近一大片皮肉都在颤抖,不知留针多长时间,牛就好了,也不瘸了。大部分牛还得针前肩、后肘,后胯这样的部位,这是不容易针进去的。牛跟人一样,有的老实,有的不让人靠近,所以往往要跟着牛兜圈子(虽然缰绳栓得短到不能再短,也有些活动余地)。牛不停地乱转,爷爷就跟着牛转,左转、右转,瞅准时机,胳膊一甩,针就插进去了,又稳又准,疾如闪电。一会儿的工夫,几根针扎好,爷爷到一旁休息去了。很快,药也抓来了,又忙着灌药。药是怎么加工的,我没看见,只见把药汤盛在面盆里,再打上二十多个鸡蛋的蛋清,混合好,找来一个盛一斤的空酒瓶,装上药汤,这次牛不是栓,而是把牛头从脖子部位捆到树上,不松不紧,头向上仰着,扒开嘴,酒瓶续进嘴里,一瓶药,一点不撒就灌进去了,一盆药,很快就灌完了。所以给牛吃药不叫吃药,叫灌药。现在的兽医站给牛看病,又是切口,又是打针,切来切去,就给治死了。我爷爷可没这样的事儿,每次都是病着来,好了牵着走回去。我爷爷给牛看病,从来不跟人索要诊费,几乎都是白尽义务。最大的收获,就是牛吃剩下的鸡蛋黄,拿回家,让我奶奶给炒炒,喝点小酒,就是他的享受了。 如果牛病得不能走路,人家就来请他上家里去治,这时候通常要管一顿饭的。这时候,爷爷就先跟主人说,“我不吃荤,别买肉了。买斤鲜鱼吧,把灌牛剩下的鸡蛋黄炒炒就行了。”这样,给主人家既省钱,又省事。忙活一天,也就挣这一顿饭吃。上我家来治的,连这顿饭也没有。大部分都是这样,也有厚道人家记得大恩,逢年过节时,像六月六,就蒸上馍馍,买一对二斤多重的白鳞鱼,放在箢子里挎着给送来致谢。也有八月节置四色礼送来,就主要是月饼了。我奶奶收了礼,念念不忘人家的好,好像反倒是她欠了人家的情。我记得56年以前,我奶奶的橱里常有点心、白鳞鱼这样的谢礼。我那时候换牙,经常牙疼,不吃饭,我奶奶就拿点心给我吃。白鳞鱼也时常炒上一段。我娘拿刀割上一寸多长的一块。那时候的白鳞鱼大,有十多公分宽,所以这寸把长的一段,加上调料,就是一碟下酒菜了。我就跟着沾光享用。有时药里需用蜂蜜,蜂蜜打到茶碗里,稠稠的,像融化的红糖那么半茶碗,我爷爷就拿棍掘一块给我吃。后来成立了人民公社,牛都归各生产队了,就没多少人再关心牛了。生产队的牛如果死了,就分了吃肉,所以就没大有人给牛看病了。偶尔给自己队里看一次,也就是给记一天工分。记得一次卢家生产队请去治了一次牛,治好后,他们生产队给了五斤豆子。我爷爷拿回家,把奶奶高兴得说了很多次。因为那时候粮食不够吃,国家就号召多种地瓜、胡萝卜,所以整天吃瓜干,地瓜、胡萝卜,把人吃的又黑又瘦,很多人营养不良,得水肿死了。活下来的人也很多有胃病,能吃上点有粮食的饭就非常享受了。每天吃的干饭是地瓜干面的窝窝头,稀饭是煮地瓜干、煮地瓜、煮胡萝卜、煮野菜,能见着点儿粮食就高兴死了,黄豆更是金贵东西。当然,这都是散了食堂,60年以后的事了。我家的事,三天也说不完,字数限制,今天先说到这里。《家国往事》第30期播报美女主播:谢谢。
自我介绍:一个小人物,现阶段还没有惊天动地的梦想。喜欢听人讲故事,但最讨厌那些心灵鸡精汤。
想听美女主播的这期播音,请猛戳最下方“阅读原文”链接。
赞赏